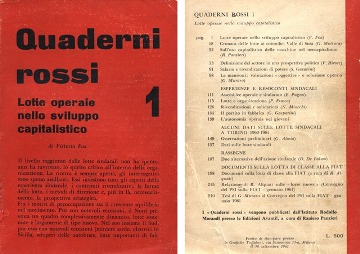我感觉肯定会和警察起冲突,当看到他们在广场中间列队,还把街道的出口封锁时,我们的队伍乱了,但在他们顶上来之后,我们的队伍又凑了起来,集结在门戈尼路和集市路的门廊下。当时的警察没有多先进的装备。不像现在的催泪弹,他们把啤酒罐一样的东西扔过来,然后在地上滚。人们用手帕保护脸,不被气体伤到,也会抓住它们往前扔,这些罐子还不像后来的催泪弹一样会烫伤手。警察还没有盾牌,警棍比现在的要短得多。他们担心受到攻击,因为布雷达(Breda)和法尔克(Falck)公司的工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一般会带头盔和工作手套上街。他们的武器也是过时的。他们把卡尔卡诺91-38式步枪当做警棍来使用。但他们更喜欢从卡车上发起进攻。他们常常失去理智开枪,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年里发生了如此多的谋杀。无论如何,在阿迪佐内事件的那一天,我们被警察扣留了三四个小时。乔万尼·阿迪佐内被一辆开进人群队伍的卡车撞死了。在最初的冲突之后,警察不再下车,因为只要下车就会被人拿棍子一顿好打。他们全速开车,让别人抓着腰,从车上挥动警棍,打中了人们的牙和脑袋。人们抄起没有杀伤力的管子(就堆放在广场上)来回应,当卡车开来时,两三个人就拿它对准驾驶员,如果卡车翻倒了——当时翻过不少——我们就跳上车揍车上人员。在某一刻,上了岁数的共产党员想停下这场冲突,但我们不同意,一直坚持到晚上,从帕多瓦军营开来了我们没法对付的大卡车。除了阿迪佐内死了,还有很多人受伤,然后晚上我们把门戈尼路的名字贴上了,改成“被警察杀死的乔万尼·阿迪佐内路”。但共产党不想让这起谋杀案成为风波。当时是中左翼在执政,共产党希望在新政治格局中分得一杯羹。在这起事件中,法官认定阿迪佐内死于逃跑人群引发的意外,党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年底我就离开了党。
就在几年前,工人农民还在示威(当时在场的少数知识分子没发挥什么作用)……(左翼政党的)政治领导人将这些力量当做筹码,谢尔巴手下警察用棍子镇压了他们,让这些人空手而归。街头示威活动越来越少,坚持下来的人只是出于守旧,或者忠于职责。
但与此同时,一支预备队正在觉醒,积攒着力量。
学生们开始从精神上接近工人,声援工人的示威游行。起初,他们只有一小群人,也不总是受到工人们的欢迎,这既是因为工人本能地不信任他们,也是因为警察对学生会手下留情(为避免麻烦)。但在1960年7月的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渐渐地,他们与年轻一代工人(农民工与本地工人)共同成为了骚动的主角。加入到游行队伍中的学生也让警察改变了做法。在放弃了幻想之后(年轻人在不可避免的“叛逆”之后,就会在资产阶级的队伍里安稳下来),警察给了学生和工人同样的对待: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打破头叫他们服软。古巴事件那一周的“骚动”,大部分是由学生组织的。一些人不巧被抓住,在受了警察几天的虐待后才被放回来。
这些年轻人和参与伯特兰·罗素
[24]的反核游行的英国青年不同,他们不是克制的守法公民……
那些为和平进行示威游行的人在今天被称为极端分子,这是有原因的。当你知道到警察从1945年至今杀害了数百名市民,打伤了五千人时,还能有什么“克制”的示威吗?因此,将示威者定义为极端分子,是塔维阿尼
[25](当时的内政部长)想要拖延警察的裁减问题,同时拒绝对流血事件负责,这不是为了诋毁骚动,只是不肯承认它们的革命性质……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