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国际体系
第一章 百年和平
十九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本书关注的是这事件的政治和经济源起以及迎来的伟大变革。
十九世纪的文明取决于四个机制。首先是势力均衡体系,一世纪以来防止大国之间的任何长期和毁灭性战争。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1],标志着世界经济的独特组织。第三是自发调节的市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福利。第四是自由国家。视乎分类方式,这些机制可以划分为经济两项,政治两项;以另一种方式分类,可划分为国家两项,国际两项。这些机制的特性决定了我们文明史的轮廓。
这四项机制之中,金本位制至为关键,这项机制的衰败是惨剧的直接原因。金本位制衰败之时,已牺牲了试图挽救金本位制但徒劳无功的其他机制。
但这体系的源头和矩阵是自发调节的市场。正是这种创新导致了一种特定的文明。金本位制只是试图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至国际领域;〔国际〕势力均衡是部份建基于金本位制的超级体系;自由国家是建立于自发调节的市场。十九世纪制度体系的关键是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
我们的观点: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意味着鲜明的理想国想法。这样的机制不可能存在而不会消灭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物质,只会摧毁人类和把周围环境变成荒野。社会无可避免要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但任何措施会防碍自发调节的市场,打乱了工业生活的组织,因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及社会。正是这种困境驱动了市场体系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明确的状态,最终扰乱了建基于市场体系的社会组织。
要理解人类历史上最深远的危机,这样的解释似乎太简单。试图把文明及其内涵和精神气质归纳为一成不变的机制,简直是缘木求鱼;选择其中一个机制,然后以这机制的一些技术质量来争论文明不可避免会自我毁灭,也只会徒劳无功。文明就像生活本身,是萌生于大量独立因素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一般不能还原为受限的机制。要追踪文明衰败的体制,可能似乎是徒劳无功。
但这正是本书要开展的工作。为此,本书刻意致力调整目标以切合极端独特的主题。十九世纪的文明独一无二,正是因为这集中在一个明确组织机制。
没有任何解释可以完满解释大灾难突然而来。似乎变革的力量已经被压抑了一个世纪,突发事件如洪流倾泻而下冲击人类。在超大范围的社会转型之上还有前所未见的战争类型,摧毁了多个国家,新帝国的轮廓浮现在一片血海。但这魔鬼般的暴力其实只是迭建在迅速而沉默的变化潜流,这潜流吞噬了过去,而往往不带一丝涟漪!对大灾难的合理分析必须考虑汹涌的行动和静默的分解。
本书不是历史著作,不是为突出事件寻找令人信服的时序,而是以人类机制来解释事件的趋势。本书自由选用过去的场景,唯一目的是要解释眼前事件;本书详细分析关键时期,几乎完全忽略了之间的时段;本书涉及多个领域以追求这单一目标。
本书首先讨论国际体系的崩溃,试图说明一旦建基于国际势力均衡体系的全球经济崩溃,国际势力均衡体系不能确保和平。这解释了这体系的突然中断以及不可思议的迅速分解。
但如世界经济崩溃是依随着文明衰败,肯定前者不是由后者引发。世界经济崩溃的源头可追溯百年前社会和科技的巨变,因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在西欧崛起。这段冒险旅程来到我们这年代走到终点,结束了工业文明历史的独特阶段。
本书最后部份讨论支配我们这年代的社会和国家变化的机制。从广义上来说,我们认为人类目前的状况应以这危机的机制源头来定义。
十九世纪的现象是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闻:从1815至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除了或多或少殖民性质的克里米亚战争;在这期间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罗斯总共只有十八个月曾彼此开战。在这之前的两个世纪,相比数字是每百年平均有六十至七十多年是战火弥漫。十九世纪最激烈的战争是1870-71年的普法战争,不到一年就结束,战败国有能力支付赔款而没有影响本国的货币金融。
这种务实的和平主义占上风,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导致严重冲突的成因。强国和伟大帝国之间的内外状况几乎时刻有变,伴随着这和平的盛会。在这世纪上半叶,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的干预措施无日无之。在西班牙,Duc d'Angouleme挥军进攻Cadiz;在匈牙利,革命军几乎打败了国皇亲临指挥的军队,最终被俄罗斯援军击败。德系国家,比利时,波兰,瑞士,丹麦和威尼斯都有武装干预,标志着神圣同盟[2]无处不在。世纪下半叶释放了进步的动力;鄂图曼帝国,埃及帝国和中东酋长帝国相继解体,中国被外国军队入侵,被迫对外开放,非洲大陆被列强瓜分。同时,美国和俄罗斯乘时崛起,成为世上两个大国。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民族团结;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成为欧洲地图的主权国家。工业文明迈进,公然入侵陈腐文化或原始民族的领域。俄罗斯军事征服中亚,英国赢得印度和非洲战争,法国侵占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叙利亚,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暹罗,引起列强之间的冲突,一般只能以武力解决。然而,这些冲突都是局部性,而无数剧烈变化的情况都被联合军事行动或列强平靖而妥协。不管是什么方法,结果都是相同。在这世纪上半叶,神圣同盟以自由之名压制自由,禁止宪政主义;到了下半世纪,有商业头脑的银行家又是以和平之名把宪制强加于动荡的独裁政制。因此,在不同形式和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之下(有时以进步和自由为名,有时由于皇位和祭坛的权威,有时受惠于股市和支票簿,有时因为腐败和贿赂,有时因为道德和开明的呼吁,有时被刺刀所迫),但殊途同归:和平得以维持。
这几乎是奇迹的事态是势力均衡无意中产生的不寻常结果。就本质而言,均衡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即是各势力单位的存活;事实上,这只是假设三个或更多有势力的单位总会与较弱势单位连手抗衡最强者增强势力。在世界历史的范畴,势力均衡关注的是国家得以保持独立。但是,为了达到这目的,各国持续开战,不断改变合作伙伴。古希腊或意大利北部城邦是这情况的实例;战斗团体不断转换成员,借着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了这些城邦的独立。同样原则的行动维护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3](1648)划分的欧洲国家主权长达两百年。七十五年后,乌得勒支和约[4]的签约国正式宣告遵从这原则,从而以体制落实并建立相互保证,以战争保障强国弱国同时存在。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是同样的机制导致和平,不是战争;对史学家来说,这是富挑战性的问题。
本书提出这是因为出现了全新的因素,即是因而衍生的和平权益。传统上,这种权益被视为在国家体系范围之外。和平以及附属的工艺和艺术只是日常生活的装饰。教会可能为和平祈祷,一如为丰收祈祷,但国家行动领域是主张动武;政府把和平置于安全和主权之下,即是为求实现意图,不惜采取最终手段。若是社会有和平权益的组织存在,这是极为不妥当。十八世纪后期,鲁索[5]指责商人不爱国,怀疑他们喜欢和平不爱自由。
1815年以后,这种变化是突然和整体。法国大革命增强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和平成为普遍关注的权益。德国政治家Metternich声称欧洲人想要的是和平,不是自由。德国人Gentz也指责爱国者是新蛮人。教会和皇室开始提出欧洲非国家化的论点,其论据得到支持,因为凶猛的战争新形式和新兴经济体系大大增强了和平的价值。
像往常一样,鼓吹新「和平权益」的人主要是权益的受惠者,即是世袭职位被席卷欧洲大陆革命浪潮的爱国主义威胁的君主和封建主义者。因此,在这数十年间,神圣同盟是积极和平政策的威慑力量和思想动力,同盟军队在欧洲四处镇压少数民族和抑制多数民族。1846年至1871年是「欧洲历史上最混乱和拥挤的四份一世纪」[6]:和平的基础不稳,应对力量消减而工业主义的实力不断增长。在普法战争之后的四份之一世纪,和平权益复苏,其载体是新成立的强大欧洲协同体[7]机制。
但权益一如意图,除非通过一些社会媒介转化为政治手段,否则只会是理想的空谈。从表面上看,没有这种实现的载体;说到底,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同体只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组合,因而受到势力均衡及其战争机制的影响。那么如何维持和平?
诚然,任何势力均衡体系往往会防止因为某国未能预见其试图改变现状所引起势力调整带来的战争。著名的情况是德国首相卑斯麦在1875年因为俄罗斯和英国的干预(奥地利对法国的援助当作是必然的)而取消对法国的新闻宣传;这一次,欧洲协同体针对德国,德国被孤立。在1877-78年,德国无法阻止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战争,但借着英国嫉妒俄罗斯可能进占土耳其内海的达达内尔海峡[8],成功把战事局限为地方战事;德国和英国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从而挽救了和平。1878年的柏林会议推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资产的长期计划,尽管这随后改变了现状,但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各路人马实际上预先知道如开战会面对什么军力。在这情况下,和平是势力均衡体系受大众欢迎的副产品。
此外,如只涉及小国的命运,有时刻意消除战争成因是可以避免开战。小国受到劝阻,以避免以任何方式改变现状和可能引发战争。荷兰在1831年入侵比利时,最终导致该国宣告中立。挪威在1855年宣告中立。在1867年,荷兰向法国出售卢森堡,德国提出抗议,卢森堡宣告中立。在1856年,欧洲协同体宣称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对欧洲的均衡至关重要,并致力维持该帝国;1878年之后反过来认为奥斯曼帝国解体是势力均衡之必需,该帝国的解体得以有序进行,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决定关乎几个小民族的生死存亡。丹麦在1852至1863年间,以及德国在1851至1856年间都威胁扰乱均衡体系,每次都是列强迫使小国屈从。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利用体系提供的自由行动的权力以实现共同权益;这共同权益正好是和平。
偶尔及时澄清势力情况或胁迫小国可以避免战争,但远远不足以维持百年和平。国际情况失去均衡,可能有无数理由:从皇室恋情到河口淤积,从神学争议到科技发明。仅仅是财富和人口的增减势必导致政治势力失衡,外部情况势必影响内部。即使有组织的势力均衡体系能够确保和平,永无战争威胁,但先要能够直接处理内部因素,在萌芽阶段防止可能出现的失衡。一旦失衡有了势头,只有动武才可以解决。老生常谈的是:要确保和平,必先要消除战祸成因,但一般没有认识这先要在源头控制生活的流程。
为此,神圣同盟有特有工具。欧洲的皇室贵族组成了国际化的亲属关系,而罗马教会在南欧和中欧为他们提供自愿的民间体制,包含从最高到最低的的社会阶梯。血统和恩赐交织成有效的当地管治工具,只须辅之以武力,就可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
但继承的欧洲协同体没有神圣同盟的封建和神职触须,至多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与Metternich的紧凑杰作毫不连贯。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召开列强会议;列强之间的嫉妒滋生了阴谋,反对意见和外交破坏;联合军事行动变得罕见。神圣同盟有完整统一的思想和目的,但依然依靠频繁的武装干预才可以维持欧洲和平;欧洲协同体较少使用武力,但可以维持世界范围的和平。要解释这惊人壮举,我们必须寻求一些在新环境中运作,又未被公开的强大社会媒介,这媒介发挥着昔日皇朝和主教的作用,让和平权益有效发挥。这个不为人知的因素是国际金融集团[9]。
迄今没有人全面研究十九世纪国际银行的性质;这个神秘体制萌生于政治-经济神话的明暗对比。[10] 有些人争辩它仅仅是政府的工具,有人反驳政府是这贪得无厌体系的工具,有人指责它是国际纷争的根源,有人认为它是柔弱世界主义的载体,削弱了刚强国家的实力。谁都不是大错特错。国际金融集团是自成一格的体系,特见于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和二十世纪初三十年,其功能是联系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为国际和平体系提供工具;和平体系得助于列强,但列强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和平体系。欧洲协同体偶尔有所行动,而国际金融集团是极具弹性的常设机构。国际金融集团独立于任何政府,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但与各方有联系。国际金融集团独立于中央银行,即使是英伦银行(英国央行),但彼此紧密相连。金融和外交之间有亲密接触;任何一方考虑任何长远计划,无论是和平或好战,必要确定对方的好处。然而,成功维护总体和平的秘密无疑是因为国际金融的位置,组织和技术。
国际金融集团人才和动机赢得的地位是牢牢植根于严格商业利益的私营领域。罗富财家族(Rothschilds,插图为罗富财家族纹章[11])不是任何国家的子民;这家族体现了抽象的国际主义原则,只是对企业效忠;在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企业信贷已成为政治政府和工业界的唯一超国家联系。在最后的情况,企业的独立性是源于时代需求要有主权的代理人,以取得国家政治家和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正正是这重要需求,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落足欧洲各国首都的犹太银行家王朝的抽象而不受管辖的特质。企业不是和平主义者;企业财富来自战争融资,不受道德考虑影响,不反对任何小规模,短期或局部战争。但如列强全面开战,影响到体系的货币基础,就可能损害业务。事实的逻辑是企业身处革命性变革中必要维持总体和平;世上人人都受这些革命变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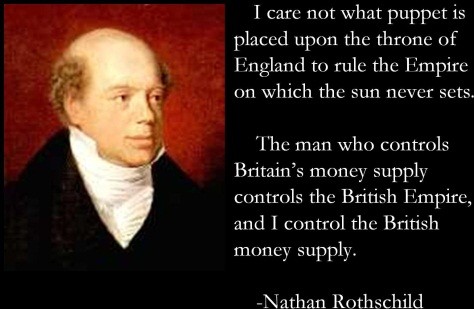 |
我不在乎谁坐在英格兰的王位管治日不落帝国。 控制英国的货币供应,即是控制大英帝国。我控制着英国的货币供应。 Nathan Rothschild[12] |
在组织方面,人类历史上一手造成最复杂制度之一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集团,虽然为时短暂,但它的丰富形式和工具是兼收并蓄,只有全人类对工商业的追求可堪媲美。除了国际金融集团中心,还有几个围绕着发钞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银行中心。此外,国际银行不仅限于对政府融资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冒险,其业务也包括外商对工业,公用事业和银行的投资,以及对外国公共及私营机构的长期贷款。各国的金融体系是缩影。单是英国已有几十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法国和德国的银行组织也是各有专注;在这些国家,财政部门的操作及其与私人融资的关系互有不同,令人诧异,其细节也颇为微妙。货币市场处理众多商业票据,海外承兑汇票,纯粹的金融票据,以及活期借款和其他证券经纪业务。各国社群和个性千奇百怪,其威望和地位,权力和忠诚,资金资产和人脉,施惠和社交氛围各有独特类型,使这模式变得眼花缭乱。
国际金融集团不是设计为和平的工具;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意外之得,而社会学家称之为适逢其会。国际金融集团的动机是收益;要实现这目标,有必要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政府目标是权力和征服。在这阶段可以忽视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忽视政府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实际上,在此期间的民族国家其特点使这样的区分没有实质意义,无论是什么目标,政府要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和增加国家势力来达致。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集团的组织和员工已是国际化,但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国家组织。作为银行家的活动中心,参与集团、财团、投资集团、国外贷款、财务控制或其他雄心勃勃的交易,国际金融集团必然要寻求国家银行、国家资本以及国家财政的合作。一般而言,虽然国家财政屈从政府的程度低于国内工业,但仍足以促使国际金融集团急于与政府保持联系。国际金融集团凭借它的位置和人员,以及其私人财富和背景,实际上是独立于任何政府,可以为新的权益服务,这权益没有本身的特定机构,也没有任何其他机构为之服务,但与社会至关重要;这权益就是和平。但不是不惜一切以任何独立,主权,既得荣誉或涉及列强未来愿望为代价的和平,但依然是和平,无须有以上牺牲就可以实现的和平。
不是为了和平而牺牲其他。势力优先于利润。然而无论这些领域是如何紧密相互渗透,最终是战争奠定了业务的法则。例如,自1870年以来,法国和德国势成水火,但这没有阻碍两国之间的交易。为了短暂目的,偶尔组成银行集团;德国银行私下投资国境以外的企业,不在资产负债表披露:参与短期贷款市场贴现的汇票和以法国银行商业文件为抵押发放短期贷款;直接投资铁和焦炭企业以及在法国诺曼底Thyssen的工厂;但这样的投资只限于法国的明确领域,而且受到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猛烈抨击;直接投资较多见于殖民地,例如德国致力取得阿尔及利亚的高质矿石,或参与投资摩洛哥。然而,1870年以后,虽然巴黎证券交易所取消了禁止德国证券的官方默许政策,不争的严峻事实是法国依然「选择不要冒险让借贷资本的力量针对自己」[13]。奥地利也受到怀疑;在1905-06年间的摩洛哥危机,禁令扩大至匈牙利。巴黎金融界呼吁要接纳匈牙利证券,但业界支持政府,坚决不支持对可能的军事对手作出任何让步。政治外交对抗持续不减。政府否决可能增加假想敌潜力的任何举措。从表面上看,不止一次解决了冲突,但内幕人士知道这只是转移到和谐表面之下的更深层次。
德国的东进野心是另一例。政治和金融混在一起,但政治是至高无上。德国和英国危险争吵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在1914年6月签署了巴格达铁路的全面协议;但很多人认为为时已晚,未能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他人则认为英德协议证明两国之间的战争不是因为经济扩张的冲突。两种观点都没有事实的证明。该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主要问题。没有英国政府同意,德国铁路线仍然未能越过〔伊拉克南部〕Basra,而条约设定的经济区势必导致两国在未来的冲突。与此同时,列强继续为大日子做好准备,这日子比他们的预测来得更快。[14]
国际金融不得不面对大大小小的权力冲突野心和阴谋;业界的计划被外交手段挫败,长期投资受损,政治破坏和暗中的阻塞阻碍了它尽力建设。国际金融集团无奈与国家银行合作,否则寸步难行,但国家银行往往是各自政府的帮凶;如没有在事前与各参与者敲定分享战利品,什么计划都是徒然。然而,金融权势也不经常是受害者,而是受惠于融资的笑里藏刀金钱外交。商业上的成功涉及以武力无情对待弱小国家,大规模贿赂落后的管理部门,以及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这都常见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森林。但出于功能性考虑,国际金融集团不得不尽力避免全面战争。如战火漫天,绝大多数政府债券持有人以及其他投资者和交易商势必成为第一批输家,特别是如影响货币。国际金融集团对列强施加的影响始终有利于欧洲和平,而且影响是有效的,政府本身在多方面也依赖这样的合作。因此,欧洲协同体从来就是和平权益的代言人,再加上各国内部的投资习惯已经扎根于不断增长的和平权益,就可以理解即使在1871至1914年间,虽然多个国家几乎动武,但始终没有爆发熊熊大火的战争。
融资是国际金融集团发挥影响力渠道之一,有力影响一些较小的主权国家的议会和政策。贷款和贷款续期是基于信誉,而信誉是基于良好行为。因此,宪制政府的行为反映在财政预算,货币的外部价值不能偏离财政预算,债务国政府要小心留意汇率和避免影响稳健财政状况的政策;非宪制政府不受国际金融集团欢迎。一旦国家采用了金本位制,这些有用的格言成为有说服力的行为规则;金本位制把允许的波动限制在最低波幅。金本位制和宪政主义是伦敦金融城向许多小国传授的工具,这些小国采用了国际新秩序这些守规符号。大英帝国耀武扬威,有时展示船坚炮利,但更经常在国际货币网络扯线。
通过暗地里管理世界各地半殖民地广大地区的财政,包括近东和北非火药库地区的衰败区域的伊斯兰教帝国,国际金融集团也得以确保其影响力。正是在这些地区,金融家的日常工作影响着内部秩序的微妙因素,为这些和平最为脆弱的动乱地区提供了实际的管理。这些地区面对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能够满足投资的无数先决条取得长期资本投资,正正是因为国际金融集团。巴尔干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史诗式的耐力和惊心动魄,让人想起北美大陆类似的壮举。但是,困扰欧洲资本家的主要风险不是技术或财务失败,而是战争 - 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很容易被孤立),也不是大国与小国之战(经常发生但颇为方便),而是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欧洲不是空洞的大陆,有千百万新旧民族的人民以此为家,每条新铁路要穿越不同可靠程度的边界,有些边界被新铁路严重削弱,有些因此而变得巩固。只有铁腕融资才可以控制落后地区的无能政府,避免灾难。土耳其在1875年拖欠债务,立即爆发军事大火,自1876年持续至1878年签署柏林条约,之后三十六年和平得以维持。这段惊人的和平时期始于1881年土耳其苏丹的「圣月宣言[15]」,在君士坦丁堡成立由债券外国持有人控制的「公共债务委员会[16]」。国际金融集团的代表被委任管理土耳其的大部份财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促成列强之间的妥协,在其他方面防止土耳其自找麻烦,在其他方面,他们只是列强的政治代理人;整体而言,他们服务债权人的利益,如可能的话,也是服务试图在土耳其谋利的资本家。这任务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债务委员会不是代表私人债权人的机构,而是欧洲公法的工具,但国际金融集团在这机制没有官方代表。但正是因为这两栖能力,国际金融集团能够跨越那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鸿沟。
贸易与和平已互有关联。在过去,贸易组织一直是军事性质和好战,是海盗、浪人、武装行旅、狩猎手、佩剑商人、武装镇民、冒险家和探险者、殖民者和征服者、狙击手和奴隶贩子,以及特许公司殖民地军队的附属品。现在这一切都抛诸脑后。贸易现在依赖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体系在全面战争中无法运行,要求和平,而列强致力维持和平。但正如前述,势力均衡体系本身无法确保和平。国际金融集团肩负这任务,而国际金融集团正正体现贸易依赖和平的新原则。
人们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完全不和平的过程,金融资本煽动了无数殖民地罪行和扩张主义入侵,与重工业有密切关联,使得列宁声称金融资本要为帝国主义负责,特别是争夺势力范围、特许权、治外法权和西方列强在落后地区取得控制地位的种种形式,以投资于铁路、公用事业、港口和重工业藉以获利的其它永久性设施。实际上,商业和金融是以往许多殖民地战争的起因,但也避免了大战。商业和金融与重工业相互联系,虽然实际上只是在德国有密切联系,但这种关系是这两项大事的根由。金融资本是重工业的顶层组织,又以多种形式与各工业部门联系,致使金融资本政策不为任何团体支配,以免战争促进了任何一项利益而损及其他利益。当然,一旦发生战争,国际资本必然是输家;不过,如战事局限于事发地方,即使国家资本也偶尔会从中获利;这足以解释几十起殖民地战争乎都是由融资者组织;但他们也安排和平。
这务实体系致力防止全面战争爆发,又借着此起彼落的小规模战争进行「和平」业务,而且改变了国际法,这正好展示其本质。尽管民族主义和工业显然会令战事变得更激烈和彻底,但已建立了有效措施以保障和平贸易得以在战事期间继续。据记载,〔普鲁士〕腓特烈大帝[17]「出于报复」于1752年拒绝偿还英国债主的贷款。美国政治科学教授Amos S. Hershey指出「之后再没有过这样的意图。…敌对行动爆发后没收交战区内敌国子民的私有财产,法国大革命战争是最后的重要例子。」[18]。克里米亚战争[19]爆发后,敌国商人被允许离港;在其后五十年,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日本和美国都遵守这措施。从这场战争开始,交战国一直颇为容忍民间自由地做生意。因此,在1898年西班牙—美国之战时,装载着美国货品(不是战争禁运品)的中立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西班牙港口。以为十八世纪的战争在所有方面都比十九世纪战争较少破坏是偏见观点。就敌国侨民地位、处置敌国人民的贷款和财产,以至敌国商人离港权利而言,十九世纪的措施显然有利保障战时的经济系统。到了二十世纪这趋势才逆转。
因此,经济活动的新组织形式是百年和平的背景。在第一阶段,新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股危及和平的革命力量,可见诸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动荡;神圣同盟鉴于国家动荡这新因素,所以组织其反动性和平。在第二阶段,新经济取得胜利。中产阶级本身此时变成和平权益的支持者,而且比反动的前人更有势力,也得到新经济体系的国内和国际特点的培育。不过,和平权益在这两方面渐见成效,是因为能够把势力均衡体系为己所用,为体系提供社会工具直接处理活跃于和平领域的内部势力。在神圣同盟时期,这些工具是得到教会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支持的封建制度和王权;欧洲协同体时期的工具是与之结盟的国际金融和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必要夸大两者的区别。在1816-46年的三十年和平时期,英国已迫切要求和平与商业,神圣同盟也没有鄙视罗富财家族的帮助。也是在欧洲协同体时期,国际金融界往往不得不依靠与王朝和贵族的联系。但这些事实只强化本书的观点:在每一情况下,和平得以维持不是简单地通过列强的大臣,而是通过为服务整体利益的有组织具体机构。换句话说,只有在新经济背景之下,势力均衡体系才能避免全面冲突。不过,欧洲协同体的成就却远远大于神圣同盟;因为后者是在稳定不变的欧洲大陆有限地区维持和平,而前者是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时成功遍及全球。这伟大的政治功绩是因为国际金融集团这特殊实体出现,是国际生活中政治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特定纽带。
至此,很明显和平组织是建立在经济组织之上,但两种组织有非常不同的一致性。所谓世界性和平组织,只有在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因为欧洲协同体基本上不是和平体系,而仅仅是受战争机制保护的独立主权国家体系。世界经济组织则与此相反。除非轻率地把「组织」惯性局限为「中央发号施令,所属职能部门执行」,否则就必须承认这组织建基的普世接受原则是最确实,其实际成份是最具体。财政预算和军备,外贸和原材料供应,国家独立和主权,都只是货币和信贷的功能。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世界商品价格是数百万欧洲大陆农民生活最核心的现实;天下商人每天都注意伦敦货币市场的波动;各国政府按世界资本市场的形势来讨论未来计划。只有疯子才怀疑国际经济体系不是人类的物质存在之轴心。因为这体系的运行需要和平来维持,势力均衡体系是为其服务。拿走了这经济体系,和平权益就从政治中消失。除此之外,没有足够原因这经济体系会存在,也没有可能保护这体系。欧洲协同体之成功源于经济体系新国际组织的需要,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其解体而终结。
1861-90年是德国铁血宰相卑斯麦主政的年代,也是欧洲协同体的黄金时期。在崛起成为强国之后的二十年,德国是和平权益的主要受益者,以奥地利和法国为代价,强势加入强国行列;出于本身利益,德国必须维持现状和防止战争,因为战争只可能是报复德国之战。卑斯麦刻意把和平的观念培育为列强的共同事业,并避免可能迫使德国放弃其和平强国地位的承诺。他反对在巴尔干地区和海外的扩张野心;他以自由贸易为武器对付奥地利,甚至法国;他借助势力均衡策略挫败了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巴尔干野心,因而与潜在的同盟国共同进退,并避开可能将德国卷入战争的情况。这位在1863-70年是诡计多端的侵略者,在1878年变身为诚实的代理人,反对殖民冒险活动。为了德国的国家利益,他有意识地领导着他认为是那时代的和平趋势。
然而,到了1870年代末期,自由贸易时期(1846-79年)结束;德国实际采用金本位制,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地扩张时代的开始。[20] 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坚强联盟,以加强本身的地位;不久之后,卑斯麦失去了德国议会政策的控制。自此之后,英国成为欧洲和平权益的领导者;欧洲依然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组合,因此受到势力均衡的制约。在1890年代,国际金融集团处于巅峰,和平似乎是前所未有地牢固。英法两国在非洲有利益分歧;英国和俄罗斯在亚洲相互竞争;欧洲协同体勉力而为,但依然发挥作用;尽管有三国同盟[21](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但依然有多个独立强国猜疑地相互监视。不久之后,在1904年,英国和法国就摩洛哥和埃及问题达成全面交易,几年后又与俄罗斯在波斯问题上妥协,形成一个对抗联盟。欧洲协同体是独立国家之间的松散联邦形式,最终被两个敌对的势力集团取代;势力均衡作为体系已经寿终正寝。此时欧洲有两个敌对的势力集团,令势力均衡的机制停止运作,不再有第三个势力集团会与这两集团合纵连环,拉一个打一个以挫败其中一个集团独大。大约在同一时期,当时的世界经济渐见败象:征兆是殖民地竞争和争取异国市场渐趋激烈。国际金融集团避免战争蔓延的能力迅速减弱。和平茍延残喘又七年,但十九世纪经济组织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为百年和平划上句号。
历史学家的要务是要认识和平建基的高度人工化经济组织其真正本质。
第一章数据参考
1. 势力均衡政策。势力均衡政策是英格兰的国家行为方式,完全是务实和实际,不应混淆「势力均衡原则」或「势力均衡体制」。这政策是英国岛国位于被各政治体系占领的欧洲大陆之外的后果。面对强大的大陆国家正在形成,历代英格兰政治家奉行势力均衡政策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唯一机会。英格兰的势力均衡政策早于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体制约两世纪,而且政策的形成过程是完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原则。然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体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英格兰的国策,因为这最终使英格兰更容易与任何在欧洲大陆领头的强国结成联盟。因此,英国政治家往往有这种想法:即英格兰的势力均衡政策实际上表达了势力均衡原则,以及英格兰奉行这政策时只是在以那原则为基础的体制中发挥本身的作用。然而,英国政治家并非有意遮掩本身的自卫政策是有别于有助推动政策的原则。Edward Grey爵士在《Twenty-five Years》表述:「理论上,当欧洲强大集团的优势似乎有利稳定与和平,英国并无异议。支持这样的组合一般总是英国的首选。只有当占优势的势力变得有侵略性以及英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威胁时,即使不是出于谨慎政策也会是出于自卫本能而趋向可被清楚描述为势力均衡的任何行动。」
因此,正是出于自身的合法利益考虑,英格兰才支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体制发展和支持其原则。英格兰这么做是其政策的一部份。以下的引文说明结合「势力均衡」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含义所引发的观念混乱。1787年,Charles James Fox愤愤不平质问政府:「英国是否不再支持欧洲的势力均衡,是否不再被人尊重为自由的保护者?」他声言英国应被接受为欧洲势力均衡体制的担保人。四年之后,Burke把体制描述为据言已生效两世纪的「欧洲公法」。这样在言辞上把英格兰国策和欧洲体制视为一致,很自然让美国人更难区分这两个同样令美国人反感的概念。
2. 「势力均衡」作为历史规律。势力均衡的另一层含义是直接以势力单位的本质为基础。在近代思潮中,Hume(休谟)首先提及。在工业革命后,政治思潮几乎整体暗淡无光,他的成果不再为人所知。Hume理解到这现象的政治本质,并强调其独立于心理和道德事实。不管动机,只要参与者的行为体现势力的作用,这现象就会发生。他写道:经验证明「不管〔动机是出于〕嫉妒的竞争或谨慎的政治,效果是一样。」F. Schuman说:「如假定多国体制由A、B、C三国组成,很明显任何一国势力上升会引起另外两国势力下降。」他推论势力均衡「其基本形式旨在维持多国体制是独立于各国。」他可以把这设想涵盖所有类型的势力单位,无论这些单位是否在有组织的政治体制之内。历史社会学实际上是这样考虑势力均衡。Arnold Toynbee(汤因比)在《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提到处于势力集团边缘的势力单位容易扩大,而是不处于中央又压力最大的单位。在西欧和中欧,实际上已不可能发生即使是细微的领土变化,但美国、俄罗斯、日本和英联邦却是扩张活动惊人。Pirenne提出类似的历史规律;他留意到最远离强势邻居的相对无组织小区一般形成抵制外部压力的核心。这样的例子有:在遥远北欧建立法兰克王国的Pepin of Herstal[22],东普鲁士崛起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组织中心。比利时人De Greef的「缓冲国」是这类型的另一个规律,似乎影响了Frederick Turner的「边疆论」,把美国西部视为「漂泊的比利时」。这些势力均衡与不均衡概念与道德、法律或心理的概念无关,只涉及势力,这揭示它们的政治本质。
3.势力均衡作为原则和体制。一旦各人的利益得到彼此承认,从中会衍生行为原则。自1648年以来,〈Munster and Westphalia条约〉确定了欧洲各国现状的利益,建立了各签署国的团结。欧洲所有强国几乎都签署了1648年的条约,宣告本身是该条约的担保人。荷兰和瑞士以签约日期作为取得主权国家国际地位的日子。自此以后,各国有权认为现状有任何重大改变将会涉及所有其它国家的利害关系。这是势力均衡初创形式的的国际大家庭原则;按照这原则,如有国家打算改变现况,无论是非对错,不会被视为针对强国的敌意行为。当然,这样的状况会极大方便形成反对这些改变的联盟。然而,在明确承认「维持欧洲平衡原则[23]」的〈Utrecht条约〉之后七十五年,西班牙领土被Bourbon和Hapsburg两大家族瓜分。这原则得到正式承认,欧洲逐渐形成以这原则为基础的体制。由于较大国家吞并(或统治)小国会打乱势力均衡,所以这体制间接保护了小国的独立。欧洲的组织在1648年,甚至是1713年之后,还是相当模糊,但在二百年间不论大小学国得以维持现况,还是必须归功势力均衡体制。无数战争是为这个名义开战;虽然毫无例外可以认为是为争取势力而战,但有许多情况与参战国是依照集体担保原则对抗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并无二样。没有其它理由可以解释清楚在绝对强大军事邻国环伺之下的丹麦、荷兰、比利时和瑞士这些弱小政治实体能够持续生存这么长时间。从逻辑而言,原则和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组织(即体制)之间区别似乎是明确的。但即便原则处于半组织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体制阶段,只是对传统习惯或习俗提出指引时,也不应低估原则的有效性。即使没有常设中心、定期会议、共享公职人员或强制性行为准则,欧洲通过各国大使馆和外交使团之间持续密切接触已形成一种体制。〔外交〕查询,外交照会、备忘录(无论是联合或分别公告,相同或不同用语)都有严格传统管制,是表达势力而不致摊牌的多种方法,亦打开妥协的新途径,或如谈判破裂,最终采取联合行动;实际上,如强国的合法利益受到威胁,共同干预小国事务的权利;以上所述等同欧洲已有半组织形式的指引。
或许,这非正式体制的最大支柱是大量国际私营企业的交易经常依据一些贸易协议或由风俗和传统形成的其它国际措施。各国政府和有权势的国民以无数方式卷入由这些国际交易引起的不同类型的金融、经济和司法困境。局部战争只意味着有些交易短时间中断,而其他交易中的各种利害关系暂时会持久或不受影响,相对于其他被战争解体,陷敌人不利的利益关系,形成庞大力量。国际互惠的无形支柱是这种私人利益,其无声压力渗透文明社会整体生活和超越国界,即使不是欧洲协同体或国际联盟这些有组织形式,它是为势力均衡原则提供了有效的约束力。
(参考书目)(略。请参见原文。)
百年和平
1. 事实。在1815至1914年这百年,欧洲列强只在三个短暂时期彼此开战:1859年持续六个月,1866年持续六周,1870-71年间持续九个月。整整两年(1853-56)的克里米亚战争是边缘地区的半殖民地性质战争;历史学家如Clapham, Trevelyan, Toynbee和Binkley都同意。顺带一提,英国人持有的俄罗斯公债在战争期间可以兑付。十八世纪和以前几个世纪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偶发的全面战争和完全没有全面战争。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少将断言十九世纪年年有战争,他的论断看来似乎无关宏旨。Quincy Wright比较多个世纪有战争的年份(无论全面或局部战争),似乎回避了要点。
2. 问题。首先要解释作为全面战争丰富源头的英法两国之间几乎持续不断的贸易战停止的现象。这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两个事实有联系:(1)旧有殖民帝国结束,(2)自由贸易进入国际金本位制时代。随着贸易新形式到来,战争利益迅速消退,与此同时因为与金本位制有关的新国际货币和信贷结构的缘故,萌生了积极的和平利益。收入和就业依赖货币稳定和世界市场,而两者的运作涉及整体国家经济体系。直至1880年,强国的一般传统扩张主义被反帝国主义趋势取代。(参见第十八章。)
然而,贸易战期间似乎有几十年的间歇期(1815-80年);在前期阶段,外交政策往往被认为促进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后期阶段,外交部长有责任关注外国债券的持有人和直接投资者的利益。正是在这半世纪的间歇期建立了私有企业利益不应影响外交事务的学说;只是在间歇期结束之时财政部长才考虑接受这说法,但在公众舆论新趋势下设下严格限制条件。本书认为这变化是由于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贸易的特点是其范围和成功已不再取决于直接的势力政策;商业逐渐影响外交政策的转向是基于国际货币和信贷体制已建立商业利益跨越国界新形式的事实。但如这种商业利益只限于外国债券的持有人,各国政府会极不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从严格意义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海外贷款纯粹是投机性质;既得收入通常是发债国的政府债券;如国民把资金贷给信誉可疑的外国政府,没有政府会认为要支持这样的最高危行为。Canning断然拒绝投资者要求英国政府关心他们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也明确拒绝〔英国是否〕承认拉丁美洲各国要取决于这些国家承认其外债。Palmerston的著名1948年公告首次暗示这态度有改变,不过从未走得太远;由于贸易团体的商业利益散布广泛,政府不能让任何不重要的既得利益把世界帝国事务的运行变得复杂。外交政策重新留意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主要是因为自由贸易结束和随后回归十八世纪的做法。但海外投资已变得不是投机,而是完全正常的性质,贸易与此有紧密联系,所以外交政策回复传统为社会的贸易利益服务。这后一阶段的事实不需要解释,要解释的是在几十年间歇期内这些利益的中断。
[1] gold standard
[2] Holy Alliance
[3] Treaty of Munster and Westphalia
[4] Treaty of Utrecht
[5] J. J. Rousseau
[6] 原注1:Sontag, R. J.,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1871-1932, 1933.
[7] Concert of Europe,中译有:欧洲协调
[8] the Dardanelles
[9] haute finance
[10] 原注2:Feis, H.,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1930, 本书经常引用参考。
[11]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b/b8/Rotschilds_arms.jpg/220px-Rotschilds_arms.jpg
[12] http://www.sott.net/image/image/s5/103815/medium/NathanRothschild.jpg
[13] 原注3:Feis, H., op. cit., p. 201.
[14] 原注4:参见本章〈数据参考〉
[15] Decree of Muharrem,土耳其(奥图曼帝国)的债务由£191,000,000减至 £106,000,000,但需以盐税,烟草税等等作为还债抵押。
[16] Dette Ottomane。
[17] Frederick the Great
[18] 原注5:Hershey, A. S.,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Organization, 1927, PP. 565-69.
[19] Crimean War
[20] 原注6:Eulenburg, F., Aussenhandel and Aussenhandelspolitik.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Abt. VIII, 1929, p. 209.
[21] Triple Alliance
[22] 丕平二世
[23] ad conservandum in Europa equilibr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