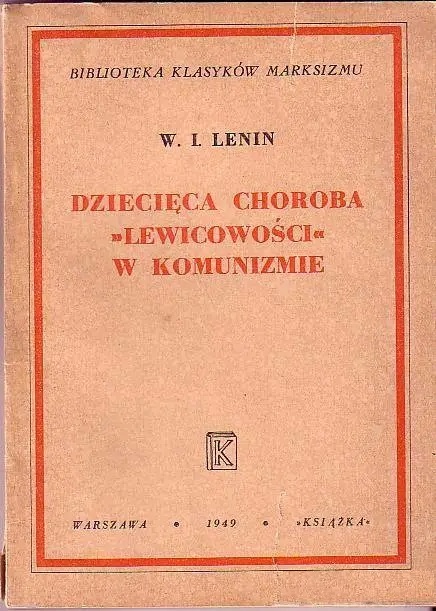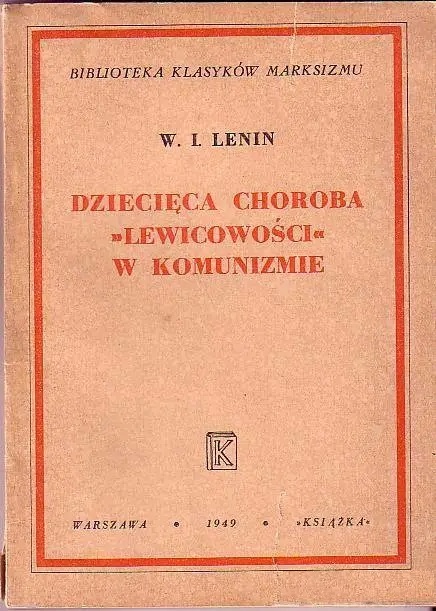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ПОЛЬ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 "ДЕТСКОЙ БОЛЕЗНИ ЛЕВИЗНЫ В КОММУНИЗМЕ"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波兰文版序言
列夫·托洛茨基
1932年10月6日,普林基波岛
Zveza 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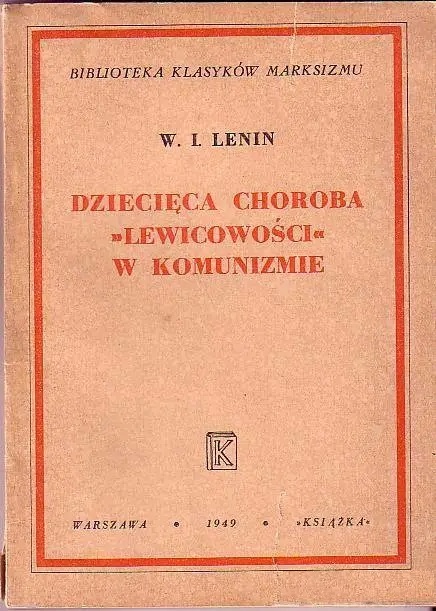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波兰文版封面
这本提供给波兰读者的列宁作品写于1920年的4月和5月。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走出幼稚的阶段,幼稚病确实是它的弊端。
列宁谴责形式上的“左派”,谴责他们做出激进的样子而空谈激进,但他同时更加热情地捍卫了阶级政治中真正革命的不妥协态度。唉!这并不能让他不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滥用,在本书出版后的12年里,这些人成百上千次地提到过这本书,用它来为毫无原则的调和主义辩护。
现在,在世界危机的条件下,许多国家的左翼正在脱离社会民主党。这类派别跌进了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裂缝里,它们经常宣称说它们特殊的历史任务是建立“统一战线”,甚至是更宽泛的“实现工人运动的团结”。这个调和的口号实质上不过是和塞德维茨、K·罗森菲尔德和老雷德布尔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长着同一副面貌。就我据此能够得出的判断来说,由约瑟夫·克鲁克博士[2]等人组成的那个波兰政治派别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类理论家一遇到事情就很喜欢引用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只不过他们忘了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又老是把列宁看成是个无可救药的分裂分子。
列宁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质是,要具备斗争的、毫不妥协的纲领与组织,与此同时让无产阶级有可能以紧密的队形向前实际地迈出哪怕是一小步;但在群众实际迈出这一步的基础上,列宁坚决追求的并不是掩盖和缓和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之间的政治矛盾,而是正好相反,是要揭露这些矛盾,让群众知晓这些矛盾,从而加强革命的一翼。
统一战线的问题也就是战术的问题,而我们知道,战术要服从于战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决定了我们的战略路线。我这样说不是要低估战术问题的意义,没有相应战术的战略必然会是脱离实际、死气沉沉的抽象概念。但是,把一个特别的战术办法——无论它在某个特定时刻有多么重要——变成灵丹妙药、变成包治百病的处方、变成一种宗教信仰,这种行为也是一样的无可救药。要革命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同毫无原则的调和主义彻底决裂。
列宁的这本书似乎是给了虚假的激进主义一记致命打击。共产国际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一致同意把书中的结论变成大会的决议。但在下一个时期,也就是大致从列宁生病和去世那段时间开始算的那个时期,我们就观察到一个初看起来有些惊人的现象:极左倾向又露头了,它在积攒力量、带来一连串灾难,然后从舞台上消失,以便下次能够以更加突然、更加恶劣的形式重新出现。
拘泥于形式,提一些平庸的异议,反对同改良派达成任何协议,反对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工会运动的团结,想建立他们自己的“纯洁的”(列宁是这么表述的)工会,并且为此提出一些肤浅的论据——虽然现在阐述这些“极左”想法的不再是幼稚的假声,而是官僚的男低音,但这并没有让它们变得更严肃或是更聪明。这惊人的旧病复发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政治潮流并不是空中楼阁。如果偏差和错误持续不断、长期存在,那就必然有其阶级基础。讨论“极左派”而不去确定它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在用概念游戏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此同时,从右边,也就是用机会主义态度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比如布兰德勒派,至今还把共产国际的一切错误归结为简单的意识形态误解,把“极左派”当成超脱于社会和历史之上的因素、一种神秘主义的因素,就像是诱惑虔诚基督徒的邪灵。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些事件彻底地表明,个别人和团体曾经犯下的那些错误实际上只是体现了一个不成熟的政治时代,而现在却上升为一种规矩,成了官僚中派主义这一整个政治潮流自觉地用来争夺统治权的武器。至于说“极左思想”是无形体的幽灵就更不对了,因为正是现在这个领导着共产国际的政治派别在让“极左”的错误和拙劣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替出现。在某些时候,斯大林派甚至不是有间隔地交替使用激进主义和机会主义,而是根据派系斗争的不同需要而同时使用二者。
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一方面,他们从原则上拒绝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目睹了反战大会的召开,他们为此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和平主义者达成了协议,同法国的激进党成员和共济会会员达成了协议,又或者同巴比塞[3]这类自命不凡、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联合起来”的独行侠达成了协议。
为了支持“协议”、“妥协”、不可避免的让步等等,列宁提出了简洁而又一如往常那般详尽的论据,它们也无可比拟地说明了哪一条界限是这些方法不能逾越的,否则它们就会转变成自身的反面。
统一战线的战术并不是普遍的原则。它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标准:以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为基础,把无产阶级先锋队联合起来。领导的艺术就在于,每次都要根据具体的阶级对比关系来决定和谁、为了什么目的、在哪种限度上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什么时候又必须把它解散。
※ ※ ※
假如我们要找一个充分的例子来说明,在哪种状况下不应该也不能推行统一战线政策,那么“全体阶级和全体党派的”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准确点说,是再坏不过了。这个例子值得逐点分析研究。
1.共产党在任何协议当中都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下公开发言,不管这协议是短暂还是持久。而在阿姆斯特丹,连政党本身都完全不被允许出现,就好像反战斗争不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也不是党派的任务;就好像这项斗争不需要最为清晰和准确的思想;就好像除了政党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组织能就反战斗争的问题给出最清楚、最完整的决议。然而与此同时,把各个党派排除出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正是共产国际!
2.共产党要建立的统一战线不是要联合个别律师记者,不是要联合赞同我们的熟人,而是要联合广大的工人组织,所以首先是要联合社会民主党。然而与此同时,与社会民主党形成统一战线的选项事先就被排除了。连对社会民主党进行号召,也就是公开测验社会民主党群众对他们领导人的压力水平,都成了不能容许的行为。
3.正因为统一战线政策中包含着机会主义的危险,所以共产党必须要排除各种各样模棱两可的调停和背弃群众的外交。然而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却认为需要提名法国作家巴比塞来当正式的领导人和幕后的调解人,让他来做旗手,哪怕他依靠的是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中最坏的渣滓的支持。在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但显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授意——巴比塞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4]就大会问题进行了谈判。但不是已经禁止自上而下建立统一战线了吗?巴比塞的调解证明,其实是允许这么做的。不用说,第二国际的头目们在耍政治手段方面肯定远远强过巴比塞。巴比塞的幕后外交让第二国际能够以最体面的借口避免参加大会。
4.共产党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让软弱的盟友——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盟友——参加到事业当中,但这么做的时候不能疏远工人群众,也就是主要的“盟友”。然而与此同时,个别资产阶级激进党成员,也就是帝国主义法国的执政党成员却参加了大会,这不能不使得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疏远共产主义。也很难向德国无产者解释,为什么可以和赫里欧[5]那个党的副主席或者是和平主义的朔纳伊赫将军[6]并肩前行,又为什么不允许向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提议共同进行反战行动。
5.统一战线政策当中最危险的事就是和徒有虚名之辈打交道,把假同盟当成真朋友,进而欺骗工人。然而与此同时,这恰恰就是阿姆斯特丹大会的组织者已经犯下和正在犯下的罪行。
现在的法国资产阶级完全就是“和平主义者”。这不难理解:每个胜利者都会试图阻止失败者发动复仇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四处为和平寻求保证,也就是要确保掠夺来的东西不可侵犯;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翼甚至准备要在同共产国际偶尔达成的协定当中寻求这样的保证。但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这些和平主义者就都会站在他们的政府那一边。他们会告诉法国工人:“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地争取过和平了,甚至连阿姆斯特丹的大会都去了;但我们还是被迫参战了——我们是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和平主义者参加这样一场实际上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大会,这在战争来临的时候只会完全有利于法国帝国主义。而另一方面,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如果在掠夺世界这个含义上爆发了一场争取“平等权利”的战争,朔纳伊赫将军以及同他一样的人会完完全全站在他们的德意志祖国那边,并且为了它的利益而利用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赢来的威信。
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帕特尔参加大会的原因和蒋介石“只有发言权”地参加共产国际的原因一样。这样的参与必然会提高“民族领袖”在人民群众眼中的威信。而对任何在会议上把帕特尔和他的朋友叫做叛徒的印度共产党人,帕特尔都会这么回答:“如果我真是叛徒,我在阿姆斯特丹就不可能当上布尔什维克的盟友。”斯大林派把印度的资产阶级武装起来,反对印度的工人。
6.为了实用目的而做的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做出原则性的让步、隐瞒本质上的分歧,也不应该接受模棱两可的表述,因为这会让每个参与者都能对它做出自己的解释。然而与此同时,整个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宣言都建立在阴谋诡计和模棱两可之上、建立在文字游戏之上、建立在掩盖矛盾之上、建立在没有实际内容的骄傲诺言之上、建立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庄严宣誓之上。资产阶级政党和共济会的成员“谴责”资本主义!和平主义者“谴责”……和平主义!就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朔纳伊赫将军在W·明岑贝格[7]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自称为和平主义者。或大或小的资产阶级谴责完资本主义之后又回到了资本主义政党的队伍中,并且表决通过了对赫里欧的信任案。这难道不是卑鄙的伪装么,这难道不是可耻的骗局么?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不妥协在采用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是必需的,而当情况涉及到像战争这样尖锐的问题时,它会变得加倍甚至是三倍地必需。对德国革命来说,一个李卜克内西在战争时期发出的坚决声音比独立社会民主党那一群和平主义者感性的半抗议要重要得多。而在法国,连一个李卜克内西都找不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在于,法国的和平主义——不管是共济会的、激进党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工团主义的——形成了一个密布着谎言和伪善的环境。列宁的要求是,不要在各种“反战”大会上为了联合而寻找共同立场,相反,要把问题说得够清楚、够明确、够尖锐,让和平主义者焦头烂额地撤退——从而给工人们上一课。因此,列宁在1922年给海牙反战大会苏俄代表团的指示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中有几个人会用几种外语发表反战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8]
稍微想象一下,列宁和法国的激进党人G·贝热里、德国的朔纳伊赫将军以及印度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帕特尔齐心协力,在阿姆斯特丹投票通过了一份大吹大擂的空洞宣言。这幅画面看起来怪异反常,而这就最能说明,列宁的徒辈究竟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 ※ ※
在列宁的这本书中,没有哪一个说法是我们现在需要去否认的。但这部作品是12年前写的。列宁的政策不断受到歪曲,列宁的语录也被滥用——在此基础之上,官僚中派主义这一整个派别形成了,而这种派别在列宁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并不存在。
斯大林主义派别绝不是没有形体的鬼魂,它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却受到孤立,由此发展出了有数百万人的官僚机构,官僚自身的等级利益又发展出了其中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但是,这是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而且被资产阶级世界所包围,它每走一步都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官僚发生敌对冲突。在决定共产国际的方向时,苏联官僚会把自身处境的矛盾烙印在共产国际的身上。徒辈领导层的全部政策就是在机会主义和冒进主义之间来回摇摆。“极左”已经不再是一种幼稚病了,它已经成为这个日益阻碍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发展的派别用以自保的一种方法。现在,与官僚中派主义作斗争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职责。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对列宁的这部杰出作品能够以波兰文出版表示热烈欢迎。
[1]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中间马克思主义政党。1931年秋,该党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分裂而成,当时有20000名党员。自1933年起,该党被纳粹党禁止,并开始在地下反对纳粹党。——译注
[2] 约瑟夫·克鲁克(1885—1972)是一位犹太记者和政治家,他战前长期在波兰活动,是波兰锡安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译注
[3]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法国共产党党员。曾经多次参加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大会和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等一系列反战工作。——译注
[4]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因1916年刺杀奥地利总理卡尔·冯·施图尔克而闻名。他于1921 年参与成立了第二半国际,并在1925—1940年间担任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总书记。——译注
[5] 爱德华·赫里欧(1872—1957),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919-1957年间三次任法国激进党主席,为该党公认领袖。1932年,他和苏联驻法国大使在巴黎签署了《苏法互不侵犯条约》。(法语人名Herriot在现代人名翻译中译作“埃里奥”,但在指该政治家时约定俗成译作“赫里欧”。)——译注
[6] 保罗·冯·朔纳伊赫(1866—1954),德国少将、男爵和和平主义运动的领袖,曾担任德国和平协会的主席。——译注
[7] 威廉·“维利”·明岑贝格(1889-1940),德国共产党政治活动家,1919年至1920年担任青年共产国际首任主席,1921年建立国际工人救济会。魏玛共和国时期为德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家。30年代后期,由于大清洗对苏联失望,流亡至法国巴黎展开反法西斯活动,德国入侵时被爱德华·达拉第政府逮捕,越狱后死于圣马塞兰。——译注
[8] 列宁《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1922年12月4日。——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