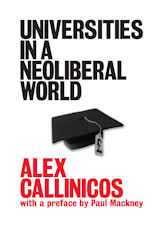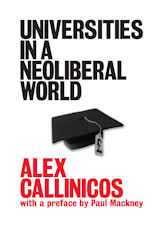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新自由主义世界中的大学
Universities In A Neo-Liberal World
阿列克斯·克里尼克斯
(2006)
周宏芬译
* 阿列克斯·克里尼克斯(Alex Callinicos)是英国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成员,伦敦国王学院从事欧洲研究的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包括《美国权力的新官僚》(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批判的资源》(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序言
自从1998年以来,作为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UCU)联合秘书长以及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教师协会(NATFHE)前秘书长,我多次谈到过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生和协会会员们的一些体验。阿列克斯·克里尼克斯则帮助我们将我们在高等教育中的经历和实践加以理论化。
当前,我们正目睹着一个卑鄙的景象:许多前学生激进分子组成的内阁,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从来不用付学费,还可以领取助学金,但他们对当前的年轻一代学生过河拆桥。当杰克·斯特劳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NUS)主席领导我们为增加助学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愤怒地指责政府逼着大学生们不得不在一本书和一餐饭之间进行取舍。在如今的21世纪,大学生们则不得不在完成作业和在超市多当一个班之间作出抉择。
全国学生联合会和高校教师联盟在抵制高校增收学费上面达成了一致,他们指出高额学费将把某些社会群体挡在大学门外。学费的增加使高校扩招出现倒退趋势,今年(2006年)的大学入学申请几乎减少了4%。我们曾经告诫说: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将会导致学生选择最便宜而不是最适合他们的课程。我们认为,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应该基于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不是支付能力。
这就是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以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一起抵制学费不断上涨的原因。全国学生联合会也支持英国高校联合会为教师争取合理收入的斗争。但如果我们要向前看的话,我们就需要再次重申从根本上反对高校收费这个问题。在19世纪,扩展了免费基础教育;在20世纪,扩展了免费中学教育;那么,在21世纪就应该扩展免费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接受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应该成为一种人权而不是一种特权。
虽然部长们一直声称由于缺乏资源(如果没有学生学费的话)而无法扩展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但是学生和老师们——事实上大部分普通人都能看出来,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其实这仅仅是一个优先次序问题。政府完全可以削减战争预算。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可以省下来一大笔钱。在工党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之前,我们曾听说戈登·布朗有一笔用于高等教育的专项资金。或许我们太天真了,但无论是我们还是部长们都想不到他会将其浪费在一场非法且没希望获胜的战争上。
和19世纪一样,政府、企业和商界领导人对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持有一种矛盾心理。在当时,他们需要一批接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去操作新机器,但是他们又不想在这方面投资。许多人坚持认为,由于工人和农民不够聪明而无法学会读、写与计算。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担心如果他们为此投资,其结果可能非常危险——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
直到20世纪60年代,工人阶级只能接受到技能教育。大学里面主要开设一些传统专业(医药、法律、政治和宗教),并且会让一部分精英拥有管理大英帝国的优越感。从传统上来看,教育理论家通常将专业培训与大众教育区别对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1世纪,资本主义将两者合而为一,因为大众教育为所谓的知识经济提供其所需要的解决问题型的劳动力,不过它是通过一种廉价的方式达到的。
作为第一批必须交纳大学学费的这一代学生,恰恰就是他们对伊拉克战争深表不满,就是他们参与了各种社会运动,比如欧洲社会论坛;就是他们参加了反法西斯组织的纠察队,这可真是历史的嘲讽啊。可是我依然坚信,正如他们赢得了关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辩论那样,他们这一代也会寻找到组织抵抗的新方式。就像阿列克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一代年轻人在法国和希腊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向他们展示了这种抵抗方式,同时,阿列克斯的这本小册子也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以便对应该如何达成目标进行讨论。
在我写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的12万名成员能选出新的领导层,使他们能够与学生们一起,为争取免费的全方位中学后教育并肩战斗。虽然创造历史并非是简单的意愿之事,但是只要人们组织起来,就能改变世界。请把这个观点传扬下去,这是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组织起来:在一起,我们就能改变世界。
保罗·麦克内
2006年11月
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协会秘书长 1997-2005
英国高校联合会联合秘书长 06/2005-06/2006 |
导论
英国的大学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为明显的标志是高校的扩招。在2004-2005学年度,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已达2287540。[1]在英格兰,如今有30%左右的18到19岁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而相比之下,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大约只有7%。
大学教育已经不再是少数群体的特权——尽管对于来自体力劳动阶级背景的人来说,进入大学仍然相对比较困难。[2]
一些秉承精英主义理念的人拒绝高校扩招,他们重复着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一句口号,那就是“多则滥”。因此,右翼专栏作家彼得·希金斯谴责前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发起了当前的高校扩招,他认为此举措是“对教育质量的又一致命打击”。[3]相反,新工党政府则宣称高校扩招关乎社会正义:“应该让所有那些有可能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的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是构建公正社会核心范畴的基本原则,因为教育是使人们脱离贫困、改变弱势的最佳且最可靠的途径。”[4](p.68)
毋庸置疑,扩展高等教育是一个崇高的目标。精英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只要能提供合适的资源,那就没有理由不实现政府提出的目标,即让50%——或者事实上更多——18到30岁之间的人接受大学教育,并从其学习经历中获益。但是,高等教育的现实与官方所宣称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相去甚远。
事实上,英国的大学目前被一些大公司需求的优先次序所驾驭。为了给英国及国外的大公司提供其需要的学术成果和技术人员以确保这些公司盈利,英国的高校正进行重组。同时,高校也正由学术机构转变为盈利机构,为英国经济挣得了很多外汇。
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国高校以廉价的方式完成扩招,具体表现为每个学生可用的资源被大幅削减,大学、院系和学者之间被鼓动着互相展开竞争。助学金变成了学生贷款,高校开始收费,这迫使很多学生必须长时间在外打工以支持他们的大学生活,为日后成为雇佣劳动者作好准备。因而,那些来自于较为贫困家庭的学生被阻隔在大学门槛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校的这种转变绝不是单一现象。全世界的高校现在都被迫进行类似的转变。高等教育的调整是更为广泛的(事实上可以说是全球性的)经济政治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一进程被美誉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力求使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遵循市场逻辑,并要求把所有东西都转化为商品,从而可以做到私有化并进行买卖。新自由主义由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并几乎被世界上每个政府及商业媒体精英所接受。
根据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观点:“事实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浪潮是与经济精英们权力的重构和重建相关联的。”[5](p.15)这种“阶层权力重建”导致了大量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进而流入这些社会精英手中。
在美国,前1%的美国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份额比,在1917-1940年期间,平均为16.9%。到1973年,这一份额降到了8.4%,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份额又一路猛增,在2001年达到了19.6%。对于处于底层的90%美国家庭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2年,他们的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份额减少了12%。[6](pp.iii,1119)在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并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停留在历史最高点。[7](p.24)
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引起了不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调整,其中就包括了高等教育。这种调整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学者和其他大学员工越来越难为知识本身而探求知识,越来越难以满足学生的教育及其他方面的需要。他们还发现,相比于其他行业,他们的收入降低了。尽管官方宣称学生是高等教育神圣的“消费者”,但由于大学要依从市场需求的优先次序,学生事实上也是受害者。
幸运的是,新自由主义在高等教育中越来越受到抵制。2006年春天,在大学老师和其他员工的帮助下,法国和希腊的学生们成功地抵制了政府亲市场化的“改革”。虽然英国没有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为了抗议低薪,英国大学的老师们也进行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联合抵制运动。这些抗争展现了这场始于西雅图和热那亚的全球性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景象。
但是,要挫败新自由主义并代之以一种不同的观念,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本小册子则可以帮助这些运动认清对手的本性,并帮其指出斗争方式。这本小册子不仅仅是基于其中引用的事实和数字,它同时也是基于我个人的亲身体验。我在英国的大学任教已经超过25年,因而亲身体验到了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这些转变。
但我抨击这些转变并不是出于对理想主义昔日的怀旧之情。我并不想要退回到若干年前的那种少数化、特权化的大学体制。对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的抗争应该成为追求公平社会斗争中的一部分,从而真正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去实现自我。因此,我的理论框架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析之上。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特别抽象的资本逻辑。因此,为了建立更好的大学所进行的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分离开来。
新自由主义和“知识经济”
英国大学当下的变革始于1979-1997年的保守党执政期间。不过新工党更加死心塌地地接受了对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这一使命。这部分反映了托尼·布莱尔个人执政方针的普遍要旨(现在戈登·布朗也赞同这一要旨),即强制通过相关政策对某些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改革,这些甚至连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没敢去尝试。当然,这也与教育在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密不可分。
以上做法的核心理念来自于“知识经济”。布莱尔政府最早的政策文件之一就是工业贸易部的白皮书,题为《我们的竞争性未来:建构知识驱动型经济(1998)》,这是由彼得·曼德尔森在其短暂且不怎么光彩的英国工贸部工作期间颁布的。查尔斯·里德比特(托尼·布莱尔的前顾问)认为支配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是:
“知识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动力,它推动产生新观念,并将这些新观念转化为消费者想要的商业产品和服务。新知识从创造、传播到开发,这一过程在背后推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它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把我们看做这个过程的消费者和工作者。如果我们要背弃经济全球化,也就同时抛弃了知识经济的巨大创造力。[8](p.10)
事实上,知识经济理念已经有点儿像目前全球政治和商业精英们的陈词滥调。总体来讲,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在知识经济中,正在发生着从实物生产到非物质化服务生产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其结果就是生产变得更加“知识密集型”——换句话说,产品的售出归功于日益精湛的制造技术,归功于产品所体现的理念,以及产品推销的理念,这些都依赖于高素质工作者所做的研究。
·因此,公司和国民经济的成功不再依赖于他们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所添置的厂房设备,而是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人力资源的技能、知识和想象力。成功地运用这些技术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个人才能成功,公司和整个国家才能繁荣。
这些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那个所谓的“互联网繁荣”时代尤为流行。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股票行情的飞扬令人产生一种欣喜的信念,即这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能将全球性资本主义推向无限繁荣的未来。尽管在21世纪初美国遭受了经济危机,但是对知识经济的信念没有动摇。比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了一本广受赞誉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可以将2000年作为全球化“全新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新时代中,“软件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应用程序,全球性的光纤网络使得户户为邻,从而使个人可以参与到全球性的合作与竞争当中——这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力”。[9](p.8)
我并不想通过这本小册子来批判那些理论家(比如里德比特和弗里德曼)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美好图景,因为我已在其他地方做过了相关的批判论述。[10]然而,关于知识经济,我认为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有关从实物生产到非物质化服务生产转变的观点需要谨慎对待。毕竟,近来一些市场成功的神话,比如手机和mp3播放器,都与新的实物产品有关。
其次,经济要取得成功,仍然需要致力于生产和出口制造业产品。最近,《金融时报》的一则有关德国的报道指出:“没有其他任何工业国家能像德国这样,成功地抓住了彼此互相关联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机遇。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中型经济体,虽然常常被描绘成一种满怀抵触、规避风险并循规蹈矩的形象,但自从2003年以来,它取代美国并一直保持着全球最大的产品输出国地位。”[11]德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产品出口国,是因为它一直在为全球性生产网络提供关键部件,而中国则是通过为这种全球化生产网络完成最后的产品组装,进而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产品出口的成功未必就能带来工作保障或繁荣。德国长期遭受着失业问题的困扰,目前的失业率达到10%。或许更令人惊奇的是,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亚洲也面临着失业增加的危险。《金融时报》报道引述了亚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的观点:
在这个拥有17亿劳动力的区域,由于就业机会增长速度缓慢,甚至连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国家也无法满足其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从而导致了5亿人失业或只能半就业。而在未来10年中,还会有另外2.45亿劳动力将加入劳动力大军……
虽然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成功地带来了许多要求高技术同时提供高工资的“好工作”,但是其他国家,尤其是南亚地区国家,却并没有取得成功。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在过去的20年中,尽管亚洲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然有几乎19亿的亚洲人口处于每天不足2美元的生活水平线下,这些人要么是没法找到工作,要么是即使工作也收入甚少。
银行指出,由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性劳动力大量过剩”,再加上各公司带着“出于意识形态的热诚”追求其竞争力,就引发了所谓的“竞次战略”。
阿里先生警告说:“大量失业或者半就业工人组成了‘后备大军’,他们为了生计而寻求就业,因此往往会接受低于标准的薪酬待遇,这就会给经济造成很大压力,从而导致亚洲的经济成功早晚会黯然失色。”
在中国,要创造就业机会日渐艰难。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估算,要达成就业率1%的增长,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为3%,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要达成同样的就业率1%的增长,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12]
在一些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率的增长尤其令人失望。这些部门往往属于资本密集型,而且其员工合同也规定了要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稳妥的工作保障。
因此,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竞争力和收益率(资本主义成功的衡量标准)与员工及穷人的福祉之间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新自由资本主义确实需要一批高技术工人,但它同时也要求在北方富裕国家和南方国家中都存在大量的低薪劳工。这些劳工只有很少的工作保障,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保障,还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
然而,“知识经济”理论家们还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成功和失败也许至多只是部分地与他们自身的行为相关。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末,新经济的繁荣引发了对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的投资。这些投资数量十分巨大,根本不能指望通过这些投资获得良好回报。比如,美国铺设的光纤光缆达到3900万英里,这些光缆足以绕地球1566圈。[13]
就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样,这种过度投资必然会导致行业的不景气。如今,许多信息技术和通信公司仍然由于其行业不景气而步履维艰,而往往是那些“传统经济”公司正欣欣向荣——尤其是对于类似石油、天然气、钢材和采矿等行业来说,随着全球对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相关产品的价格也随之增长,从而使这些行业从中获益。确切来说,这些公司并不太符合知识经济的理论。但是在10年前,情形则截然相反,并进而引发了知识经济理论的创立。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确实是由竞争驱动的。竞争是一个盲目的过程,竞争的结果既无法控制,也无法(在任何细节上)预测。
竞争的另一个特点不但被知识经济的拥护者们所忽视,同时也被大学校长们所忽视。这些大学校长们称他们的学校为“世界卓越中心”,或者其他各种称号。但有竞争就会有赢家和输家。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成为“世界卓越中心”,那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呢?就经济竞争而言,失败了或许会被别人兼并,或许彻底破产出局,而工人们则有可能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大学而言,竞争失败(起码就目前来说)或许还不意味着要关门大吉,但它确实会使学校能得到的资源份额减少,进而会使提供给员工和学生们的条件变差。
虽然知识经济理念只是为现实描绘了一幅非常片面的美好图景,但是它确实包含了一丝真理。当前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时代。每个公司都面临着提高员工生产率以降低成本的压力。由于每天只有24小时,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就依赖于公司对先进技术的投资。因此,公司有必要加大先进技术的研发的投资,增强对高技术工人的培训以使其能够设计和运用新技术。
各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也体现着这一竞争逻辑。他们经常把自身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与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大老板们和员工们一直在追求效率增益,现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新兴的巨大低成本经济体,摆在了他们面前。而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则意味着竞争逻辑已经深入内化到大学的运作方式之中了。我们将会看到,竞争逻辑使大学尽量廉价地让更多学生接受教育,并尽可能廉价地进行日益重要的研究工作。
利用知识获利
虽然工党政府的执政方针透着虚伪,但在表述对高等教育的意图时,其率真与坦诚令人称许。在戈登·布朗所在财政部的一份重要政策文件中指出:
在英国,以创新为推动力是提升未来财富创造前景的关键。在未来10年中,要想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增加就业来推动英国经济增长,那么,与过去相比,英国需要大幅增加对知识领域的投资,并要更有效地将知识转化为商业和公共服务创新。英国政府,包括其私有的非赢利性部门,都有着一个远大的目标,那就是要使英国在全球经济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中心。英国不仅要成为重大科技发现的先行者,还要做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领头人。[14](p.5)
财政部特别强调其对公共部门中的研究投资的经济效益。但它同时强调,这些研究并不能仅仅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因此就要求“研究领域有更多的经济回报”。
要使研究领域与日新月异的经济需求更好地融合,就应该支持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这就需要鼓励跨国企业对英国本土的中型公司进行投资,提升他们的研发力度,使其与行业先行者看齐;同时要通过新兴企业的创立和快速发展,孕育创立基于新技术的新部门。[14a](pp.10-11)
因为大学是“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它们要更加紧密地依从于“日新月异的经济需求”。2003年,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查尔斯·克拉克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为自己设立了三个主要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更好地利用知识来创造财富”。[4a](p.2)
为达成这一目标,前《金融时报》编辑,现英国工业联合会理事长理查德·兰博特曾被布朗委任去探索如何加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这项任务体现了布朗对提高英国生产率的关注。长期以来,英国一直都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生产率要低。
兰博特突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其他的经济体相比,英国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在下降,而对研发的投资是生产率状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981年,英国在研发上的总投入高于七国集团中除德国之外的每一个国家。到1999年,英国在研发上的投入已经落后于德国、美国、法国和日本,仅仅与加拿大持平。”此外,英国的研发投入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行业,特别是医药学、生物技术、国防和航空工业,而在“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主要行业,尤其是电子电力、化学、工程学、软件和IT服务业,英国的研发投入都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5](pp.15,17)
这一变化也反映出了英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问题。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就长期遭受对制造业投资不足的困扰。如今的研发,也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仍有英国企业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但兰博特提到:“目前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全球化公司,它们与英国在文化和知识方面的关联都不再像10年前那样紧密。”由于跨国公司正寻求让它们的运作更靠近其主要市场,因而他们可能会将研发更多地转移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15a](p.17)
不过兰博特还指出了一个更为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关于研发的开展方式。从20世纪初开始,大公司倾向于在它们自己的实验室里作研究:例如,德国化学工业还有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就是如此。但这一点如今却发生了变化。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相关的研发要求对一系列技术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从而没有哪个公司可以单独完成。激烈的竞争甚至使得那些最大的企业也不得不减少开支,它们不得不将资金集中在它们的“核心活动”上,并削减甚至关闭它们的研究实验室。结果,这就使得独立研究者队伍极不稳定,他们甚至可以从风险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来创建自己的小公司。
但是研发对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兰博特认为,大学与国家应担负起责任,提振因企业减少投资而造成的研发不景气。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大学是企业潜在的充满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优秀的大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研究网络中开展工作:他们了解世界范围内其所在领域的前沿研究进展情况。大学实验室与公司研究机构或者公共研究机构不同。随着学生、研究生和老师等新研究成员的不断加入,他们给大学实验室注入了‘新鲜血液’。”[15b](p.18)
正如美国企业学者亨利·加斯柏所指出的那样:
公司实验室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完成了大量的创新,由于这些实验室的研究重心不再是基础研究,因此,他们将来不可能再完成如此大量的创新活动。这就要求社会的其他方面提供未来20年用于产生创新的资源。这需要政府和大学来解决这种不平衡,大学将逐渐成为重大发现的集中地。工业界也需要跟大学合作,将这些发现转化为创新产品,并采用适当的模式加以商业化。[15c](p.11)
此外,兰博特还认为,“这种改变对英国尤为重要。在国际竞争中,英国的大学研究成果跟别国相比一直都不错,但是企业研究就要差一些。因此,对于英国企业界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如果处理得当,通过这种新的合作方式,英国的企业可以极大地增强其竞争力”。[15d](p.11)根据各种国际性的大学衡量指标,英国大学通常排在全球第二或第三的位置(美国大学一直稳居第一),这远远领先于英国企业在全球的排名。[15](p.9)因此,需要学术界来帮企业界一把。
但这样一来,又有一些方面自相矛盾。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私有企业是最好的。新工党就是依照这一基本规则,强制对医疗和教育服务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但当谈到研发的时候,由于其对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私有公司很乐意削减一些重大长期投资,并期待大学及政府可以担负起这一重任。
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特别奇怪的事。国家依赖于其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而才可以支配其所需要的资源来完成政府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那些主宰本国经济的企业,国家统治者们特别注意提升其收益率和发展。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这些公司就会惩罚他们。比如,将资本撤出,从而导致该国要从国外借钱,这会让成本变得更加高昂,也会拉低该国货币的汇率。
在布莱尔和布朗领导下,新工党政府认定,要避免这种有关资本的冲突发生,政府应该对大企业唯命是从。就跟过去一样,这仍旧牵扯到一些政府行为。这些行为通常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但是要资本家单独去完成又太过昂贵。在20世纪前半段,国家之所以承担了确保劳动力及其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的责任,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员工们会变得更加高效和顺从。
在保守党和新工党统治下,国家已经被重组——福利保障还没有被废除,但是已经被削减,并尽可能私有化;国家的专政机器——军队、警察、监狱和安全保障系统——被大大加强;社会资源被转移,以增强私有企业的竞争力。高等教育的变革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政府希望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1.86%提高到2014年的2.5%。为达到这一目标,从2004-2005年度到2007-2008年度,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公共研究经费的年增长率要达到5.8%。[14b](p.7)
这些钱拨给了大学,但并不是说大学可以将其花在任何它认为有价值的研究上。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那样,政府的目标是要“利用知识创造财富”——这是符合竞争和获利逻辑的。里德比特说得更直白:“大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而应成为当地经济创新网络的中心,比如,要帮助从大学中剥离出独立的公司。大学应该成为知识经济的露天煤矿。”[8a](p.114)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因为露天矿对环境的破坏及对矿工身体的损害之严重尽人皆知。事实上,英国高校的这种堕落已经愈演愈烈。
这一切真是历史的一种嘲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激进分子抨击大学变成了特权的象牙塔,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大学与社会的关联。[16]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采用了“相关性”这个说法。他们同样也抨击学术象牙塔,不过用的是各种不同的优先次序名义。60年代的学生运动希望对大学进行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将其从资本主义下解放出来。今天的政府和企业界也希望对大学进行改革,不过他们要求大学应全方位地依属于资本主义。
“露天开采”的大学
在英国,对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已经进行20多年了。这种重组作为一种削减政府开支的行为,始于撒切尔政府时期:控制大学经费是保守党减少公共开支努力的一部分。不过,到梅杰和布莱尔政府时期,重组的重点转移到以廉价的方式进行大学扩招上来。
这表现为:学术官僚所惯用的“单位资源”——政府资金分摊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数量——在逐年减少。这意味着大学员工的工作量增大了,因为他们必须要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提供教学和其他服务。平均来说,在30年前,每位老师要给9个学生上课,现在则是21个——工作量增加了1.5倍。[17]特别是在一些新的大学(1992年升为大学的以前那些工艺专科学校和其他学院),由于对第一年新生的教学都是以五六百人为一组,工作量可能要比这个平均值高很多。
与此同时,大学教师的收入相对来说则在下降。从1981到2001年,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非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增加了57.6%。而在同期,旧有大学中处于讲师B级最高一档的教师,其工资增加了6.1%,而新的大学中处于高级讲师六级的教师,其工资则增加了7.6%。在2003年4月之前的10年中,大学员工的真实平均收入增加了6.6%,会计师收入增加了12.1%,中学教师收入增加了12.3%,医师收入增加了26.6%,经理和高级官员的收入则增加了31.6%。[18]
工作量还以其他形式压到学术人员身上,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在1986年保守党政府开始采用的科研评估(RAE)。这项评估两次之间相隔时间不是很有规律(上次评估是在2001年,下一次将于2008年结束),而且评估的对象则是英国每个大学院系和机构所从事研究的研究质量。
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HEFCE)以及英国其他地区的相应机构将根据这些院系和机构的排名情况,将所谓的“质量相关”(QR)资金分配给各大学(高等教育领域充斥着缩略语以及晦涩的官僚语言)。这笔钱是大学研究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如果大学不想仅仅只是充当一个教学机构的话,那么这笔钱就至关重要(在政府对研究“双重支持”的体系中,另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由国家资助的研究委员会,它为一些具体项目提供资助)。
科研评估充分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大学员工被招进来,既要从事科研,也要承担教学任务(他们工资的五分之二名义上是付给他们做科研的)。那么,如何计算他们的工作量呢?跟工业生产类似,这就需要找到某些能够量化的产出。学术上最明显的“产出”就是发表文章。但很快发现,仅仅用所著书籍和文章的数量进行衡量是不行的,因为要创作出大量的学术垃圾是相当容易的。于是,科研评估就逐渐采用同行互查的方式,由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评审组对他们同事的研究工作进行评估。每一位学术人员都还要提交四项“科研成果”,不过,这些就得根据相应标准进行评估了,比如,这些成果是不是发表在“顶级”杂志(“顶级”杂志通常都在美国)上,等等。
科研评估逐渐变成一个费钱又费时的过程,同时又充满了不合理。比如,大学千方百计不把那些“无生产力的”学术人员放到名册里,这样不会降低大学的排名。于是,一些老师就不得不签订“纯教学”的合同,这样科研评估时,他们不会再被计算到其中去。在许多方面,科研评估就跟前苏联的官僚化指令性经济一样荒谬:就像斯大林主义的企业管理者们常常试图蒙骗中央的计划制订者一样,因为大学有这么大一笔资金取决于他们的科研评估排名,那么他们当然要对自己提交的评估材料进行润色。
针对各方对科研评估劳民伤财的抱怨(2008年的科研评估预计将花费4500万英镑),戈登·布朗在2006年3月宣布,政府将简化评估体系,包括要取消目前所采用的同行互查方式,并且要基于“度量”进行“质量相关”资金的分配——“度量”是一些量化指标,比如各机构从研究委员会申请到的资金数量。[19]
这种做法将会使当前体系中的不合理现象进一步恶化。对于艺术和人文学科来说,本来就没有从研究委员会得到太多资助,这样一来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大大加强,而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的理念事实上使这一切合理化。上面所提到的评估体制不过是这种方式的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因此,就像中学教学由教育标准局(OFSTED)监督一样,大学教学也要受到质量保障机构(QAA)的集中监督。
科研评估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是使其变得更加糟糕。科研评估已经缩小到单个学术人员的研究表现。比如,在2008年的评估中,每个人的研究将会根据以下标准划分等级——“四星级: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三星级:研究处于国际优秀地位……二星级:研究得到国际认可……一星级:研究得到国内认可……未分类:忽略不计。”[20](p.31)由于排名降低的代价是如此之高,各机构都会努力将尽可能多的员工归到高等级里去,产生了各种各样荒唐的关于自己国际(为什么不是星系际?)地位的夸张说法。
科研评估是将竞争逻辑引入大学内部的一种关键机制。每个学术人员都明白,自己的职业前途将取决于自己在科研评估中的表现。于是,这就会激励他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科研,而不是把精力放到教学或者与其他学术同行的交流上。学术人员力求通过争取到研究经费来“买断”自己沉重的教学和行政管理负担。如果他们能成功的话,那么他们的教学任务将会由临时的代替者或者是研究生助教来承担。
以上只不过是促使大学日益层次化的其中一个因素。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明星机制。大学为提高自己的科研评估排名,就会竞相引进那些真正国际知名的顶级研究者。大学给这些明星们提供一些特殊条件——非常高的工资,很少或者减免教学和行政管理任务。这就造成了一个等级体制,由顶尖学者组成的超级联盟处在最顶端,大多数工作过重而报酬过低的“普通”学术人员处于中等,而处于底层的则是那些日益增加的临时员工,其中有很多是为完成博士学业而挣扎的研究生,这些人只能签订短期合同,或按工作小时数领取薪水。
不只是学者之间有这种等级制度,大学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兰博特指出,在2000-2001年,15所英格兰大学从三种主要的研究资金来源——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的“质量相关”资金、研究委员会的拨款,以及工业资助与合同——分别获得了60%到68%的份额:其中有10所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国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谢费尔德大学,以及南安普顿大学——得到了所有上述三种资金的资助。[15](p.82)
那些得不到足够研究资助的大学,除专心教学外别无选择。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当前体系中的劳动分工:如果由少数几个机构分掉了研究资金的绝大部分份额,那么其余学校(包括“顶级”大学的临时员工)就不得不担负起对日渐增多的学生的教学任务。
当然,英国大学一直都有着一种等级制度,其中牛津、剑桥一直都处在最顶端。但是,总体来讲,政府政策,特别是科研评估,强化并重组了这一等级制度。在2001年的科研评估中,各机构按照从一到五的等级进行排序,其中最高等级是五星。在这次评估结束之后,政府又提出新的最高等级为六星(在本次和上次的科研评估中都被评定为五星级的院系就是六星级),而政府也确实增加了对这些机构的拨款。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五星级院系的拨款保持不变,而所有其他机构的拨款事实上却减少了。政府实际上偷偷挪动了标杆。当时的终身学习和高等教育大臣玛格丽特·霍奇解释道:“我们希望将研究资金集中投入到世界级的机构身上,其次才会考虑那些处于上升势头的机构。”[21](p.8)
一项英国哲学学会的研究表明这种资金集中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在2006-2007年度,有1000万英镑的“质量相关”资金在哲学系间进行了分配,分配情况如下:
五星级 33634英镑(按每个在编研究活跃人员所得资金计算) (6个院系)
五级 26579英镑 (16个院系)
四级 8520英镑 (10个院系)
四级以下无 (12个院系)
高等教育的未来
白皮书阐明了这种资金集中化背后的理由: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德国、荷兰和美国(研究和学位的授予局限于1600所“四年制”大学中的200所)将它们的研究集中在少数几所大学中进行。与此类似的是,中国政府正计划通过打造10所世界级的大学来集中研究资金的分配;在印度有一个分布于全国5个地方的全国性国家技术学院。这表明,我们需要仔细考虑该如何组织我们自己的研究,以确保我们的一些研究机构有能力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机构相抗衡。[4](pp.13-14)
跟往常一样,又是国际竞争的威胁,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威胁,被用来证明重组的合理性。这种研究资金集中政策的理念,就是要建立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大学体系:有一批作为精锐的“世界级机构”,有相当大一批从事某些研究,但主要专心于教学的大学,而处于底层的则是一些类似美国社区大学的学院,主要为出身于贫困工人家庭的学生讲授一些职业课程。不平等现象在中学体系中已经非常普遍,而这种等级制度将助长这种不平等现象再现于大学机构中。
结果就是,在英国的大学中,研究大大优先于教学。无论是对机构还是个人来说,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回报都决定于其科研成绩。根据目前普遍流行的观点,在大学生申请课程时,要将他们看做是在行使自由选择权利的消费者。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基于过去20年中高等教育重组所采用的方式,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观念使得质量保障机构(QAA)的干涉合理化。这给政府提供了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监控的机制,却并没有改变整个体系的基本特点。
大学课程的日益模块化进一步弱化了教学的地位。课程被分解成大小相等并可互换的小模块,理想情况下,学生可以通过选取并组合这些课程模块来组成自己的学位。这些变化,尤其是加上采用了中古世纪的三学期制,就使学生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的学位课程可能没有任何的知识连贯性。三学期制采用美式的以15周为一个学期。这种学制的引入,就是希望能够发挥减少给学生实际授课时数的作用。
这一体制另外就意味着,如果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代价将会是非常高昂的。如果一个机构没能获得相当数量的研究经费,那么这些机构的相对竞争力很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只要表现出一点儿疲软态势,余下的一切都将随之而来——应征人数下降,研究经费缺乏,员工意志消沉,以及在将来成为一个“纯教学”机构。
因此,大学管理者们就有很强的动机使他们的机构保持尽可能高的效率以及尽可能强的竞争力。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高级学术人员会议,会上提到,一位唐宁街顾问曾经说过,英国只能支撑6所能与美国顶尖大学相抗衡的“世界级”大学。这类说法肯定会让罗素大学集团的大学校长们心惊胆战。在罗素大学集团的19所“研究型”大学中,每一所都想拼命确保他们是达到该标准的院校之一。这种焦虑将竞争逻辑更进一步渗透到高等教育中去。
竞争逻辑不止对研究领域产生作用。由于可以向海外学生——比如那些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学生——收取高额学费,这就极大激励了大学招收这些学生。海外学生的学费成为缺少资金的大学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在2004-2005年度,英国大学里有超过217000名海外学生——来自中国大陆(海外学生的最大来源,在人数上遥遥领先)、美国、印度、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学生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22]
伦敦经济学院和亚非学院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海外学生的学费,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常见,但对很多新的大学来说,由于他们得不到太多的研究资金,他们在招收海外学生方面往往特别积极主动。[23]但在招收海外学生方面,英国大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与它们的大学同行竞争,尤其是要与来自说英语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竞争。
因此,英国大学非常容易受一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政府签证政策的改变(“9·11”事件之后这成为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国际经济危机(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的海外学生生源,其本国自身高等教育体系实力的增强,例如中国。大学越把自己与全球性的国际学生市场捆绑在一起,也就越容易受到这个市场波动的影响。
竞争逻辑意味着集权式管理。要裁掉那些没有竞争力的院系和员工,并要求剩下的人承担更多的工作量,如果是通过民主辩论和民主决策的方式是很难达到的。权力需要集中到高层管理人员的手中,他们执行必要的针对员工的政策,并为此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些在英国大学里正在大踏步进行中。
在英国,大学的传统被打上看重同事关系的印记。这可能要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最初观点,那就是大学要作为一个学者团体。现在对这一点长吁短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由学者集体管理这一观念在某些最有特权的机构中最为根深蒂固,比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某些学院。在这些地方,最坏情况不过是纵容了狭隘、懒惰和酗酒的行为。但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大学体系中的共治意味着学者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管理自己的工作。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对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已经引起大学权力在其内部的再分配。已经出现了一批执行这些新政策的专门管理人员。他们有些是高级学术人员,其余的则来自其他公共部门或者私有企业。虽然他们的PPT陈述通常要用一些商业行话作为点缀,但是人们却又不能将其当成一个笑话而不予理睬,因为这些人是决策者,而且他们作决策不是基于知识价值,而是基于结果。这种模式顺着等级层层向下,于是,学术院系的领导人就变成了部门经理,他们要完成由上司及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HEFCE)、质量保障机构(QAA)和教育与技能部等各机构所设定的各项目标。
这个过程体现了政府采用商业模式进行大学运作的政策。兰博特评论特别关注到了大学管理:“许多大学正重组自身结构,并把权力从委员会转到了学术和行政管理者手中。其结果就是决策速度加快,而且管理也更加灵活。其他大学应以此为榜样,并且要采用该行业的最优方法。”兰博特特别强调了校长在其中的作用:
相比于其他任何个人,一个大学校长的眼光和管理技巧更能决定该校的未来状况和成功与否。目前,校长的角色更接近于首席执行官,其所经营业务的年营业额达上百万英镑。要为大学制定并实行可持续的长期战略和财政规划,大学校长在管理、决策——以及学术——方面都要具有相当高的领导才能。[15](pp.95,99)
当然,这种对于“领导才能”的阐释常常被托尼·布莱尔所引用,并被更多人用来将那些亿万富豪们(比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塑造成英雄。因此,校长们的装腔作势——还有他们所领取的丰厚薪水——就不再主要是个人虚荣和贪婪的问题。这反映了更明显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既然校长像首席执行官运作企业那样管理大学,那么他就应该被当做首席执行官那样对待,并且要领取首席执行官那样水平的薪水。
在2006年的薪水争执中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校长的平均年薪已经达到了15.8万英镑,这比三年前增加了25%。有33位大学校长的薪水比英国首相还高,其中有18位大学校长的年薪超过20万英镑。大学的雇主们和校长们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大学院校雇主协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s Employers Association)和“英国大学”(Universities UK)指出,“大学校长的工作要求很高,要管理一个复杂的、营业额达数百万英镑的机构,就像首席执行官那样”。“对一个成长中的行业来说,要吸引、留住并奖励那些有着足够才干、经验和天赋的人才,就得付给他们那样的报酬。”[24]同样的论调被用来证明主管工资的增长的合理性。这种增长绝对是可憎的。比如,1971年,美国顶尖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是平均薪水的47倍,而到了1999年,这些人的收入增加到了平均工资的2381倍——这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内利润或股价的增长。[6](pp.116-118)
但是,大学并不仅仅要像企业那样进行管理——他们还要被迫与企业密切合作。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得到新工党政府授意的兰博特评论特别强调了“知识转化”——大学要从事能够直接创造效益而且能被公司利用的研究。大学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在被大力提升。这种合作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大学从公司那里接到研究合同,给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设立更长期的合作项目,或者创立他们自己的“衍生公司”——为利用大学中研究的新发现而从营利角度设立的公司。
为了支持这些合作,政府引入了所谓的“第三条渠道资助”,其资金由高等教育创新基金提供。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宣布:“我们打算挖掘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潜力,使他们在完成教学使命之外,将第三条渠道活动当做他们第二项使命的重点,从而在大学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5]这份半文盲的声明意味着,一些大学将被迫去为企业工作或者开设公司,而不再只是做自己的研究。
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现在定期发布商业报告。根据《金融时报》报道,2006年7月颁布的最新一期报告指出:
英国大学正变得越来越有商业头脑。
授权和许可协议的数量猛增了198%,在2003-2004年度达到2256。在2003-2004年度,许可交易、合同科研、咨询收入和其他活动加在一起为经济发展贡献了20亿英镑。
大学在授权自身发明方面更为成功。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政策官员艾德里安·戴指出:“5年前,技术商业化对大学来说是一个新词,每个大学都被要求成立‘衍生公司’,却不知道要用公司做什么。如今,这样的公司数量少了,但质量都提高了。”[26]
一些“衍生公司”现在非常赚钱。同样是在2006年7月,由帝国理工学院成立的帝国创新公司,成为第一家在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的由大学拥有的技术转让公司。它把14%的股份卖给金融机构,从而筹集到了2500万英镑。一位善于“将高技术理念转化为盈利公司”的专家在《金融时报》上谈到,“在未来两年内,大部分英国的顶尖科研型大学将签订长期协议,以使公司能够获得大学发现和创新的专有使用权。”[27]10所机构已经签署了这类协议,“知识产权商业化公司早已忙于抢先签下其余的30所高质量大学”。[28]
无产阶级化与朝不保夕
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使大学员工和学生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变化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无产阶级化”和“朝不保夕”。这样的用词或许令人生畏,但它们所指代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状况同样可怕。无产阶级化是一个人被迫成为雇佣劳动者的过程,于是他们就要依赖于是否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卖出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要他们还要服从工作中的管理权力。朝不保夕是指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状况,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和待业劳动者能体会到这一状况——一直处在失业边缘,不得不将就着做一些非正式的、临时的或者是兼职的工作,或者要同时做几份工作。
传统上来讲,学术人员一直是一类有着特权的雇员。他们拥有社会地位,并有着相对较高的收入。他们在工作上有着很大的自主性,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有权决定如何安排他们的教学时间。这种自主性在雇佣劳动者中是很少见的。学术人员在管理大学上所起的作用则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与众不同。这些状况为大学作为一个学者团体的理念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大学里,所有的员工有着相同的利益。在一些老牌的大学里,这表现为高校教师协会(AUT)往往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行业协会,而不是工会。
19世纪末以后,大学发展成为现代机构,但是它们仍然只对一小部分人开放,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男性。这种特权情形反映在大学所发挥的作用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肩负起一种融合功能,将旧有的贵族阶层与统治一个世界帝国所需要的中上层专业人员融合在一起。陆续成立的其他大学则负责培养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研究者和专家,并为日益扩大的教育体系自身培养从业者。
这种体制的精英特色,即便在1963年罗宾斯爵士提交报告要求扩展高等教育之后,仍然幸运地得以保存。社会学家A.H.哈里斯指出,这种精英特色确保了“高校有自主权,能够自我管理,并能通过国家机制从因其生色的社会接受资助,这种国家机制是不受民主制国会审查的机制”。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在1919-1989年期间负责政府的大学拨款,“在大学和国家之间起到了桥梁和缓冲带的作用,(在教学和研究上)带有这种学术效益,并保护其免受政府控制”。[29](pp.6,176)
对于高校教师协会(AUT)经常提到的传统学者的形象,哈里斯用略带调侃的方式进行了一番描述:“先生们不受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限制。先生们没有雇主,没有工会,也不需要协商、仲裁和调解机制。先生们领取的是报酬,不在乎报酬率。先生们不仅仅是拥有一份工作,他们是在从事一项职业。”[29](p.129)
但过去25年的发展历程无情地破坏了这幅景象。学者们的收入实际上或多或少有些停滞,而相对来说是下降了。在1928-1929年期间,学术人员的平均工资是同时期制造业平均工资的3.7倍,1966-1967年变为2.1倍,而1988-1989年则为1.54倍。[29](p.131)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由于老师们不得不教授越来越多的学生,并承担日益增多的行政管理任务,他们的工作量迅速增加,其中有很多任务是通过集权的方式强加到他们身上的,而这也是政府及其代理机构管理大学的方式。与被其取代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不同,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HEFCE)只不过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而已。在其指引下,研究变成了激烈的竞争,并一直担负为科研评估发表文章的压力。机构管理方式的发展已经把权力从学术人员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委员会,转移到以校长为中心的更小的团体中。
当然,整个行业中的情况各不相同。一般来讲,“研究型大学”的中坚分子(罗素大学集团加上少数几所其他院校)情况要好一些,而为了科研评估引进的明星教授,不管他们到哪个学校,都能签到一份好合同。此外,大学院系内部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分工界限比起许多其他工作场所来还是要模糊:院系领导既是“同事”,又是“部门经理”。这可能会造成很多混乱,因为这意味着有些经理同时也是工会成员。
另一方面,相比于老牌大学中的同行,新兴大学中的学术人员过去能享受到的特权条件要少得多。比如,需要挤时间来做研究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工会,即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教师协会(NATFHE),形成了一种更为好斗的工联主义传统,并倾向于由左派领导。
在前任秘书长保罗·麦克内领导下,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教师协会确定了十分鲜明的政治立场,特别是支持“停战联盟”和“反法西斯组织”。这个传统通过协会在继续教育学院组织讲座进一步强化。继续教育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一场比大学更急切也更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结果就是给老师和学生提供的条件也恶化得更厉害。
尽管有形式上的不同,但是总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即哈里斯所说的“大学职业的逐步无产阶级化”[29](p.136)。大学教师逐渐被降格为高素质的雇佣劳动者。这一过程体现在一种意识的转变上。这种转变在那些老牌大学里的较为年长的学者身上更为明显。这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加入教师队伍,那时候,大学作为学者团体的观念还有点儿现实性的特点。[30]现在更为普遍的则是“他们和我们”的意识。这种意识通常表现为教师对政府和大学管理层的怨恨情绪。随着这种心态的变化,在老牌大学中引起了真正工会主义的兴起——在高校教师协会最近举办的一次投票中,大多数人支持采取行业行动,也赞成在2006年6月1日跟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教师协会合并,组成新的大学和学院工会(UCU)。
无产阶级化不但恶化了老师们的状况,而且还扩展到了其他员工身上。大学日渐依赖大量短期合同制员工。有些被聘为研究员或实验室人员,其他的一些则承担日益繁重的教学任务。各大学都想模仿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位知名学者开设一门课程,他只要讲好课就可以了,讨论课和辅导课的实际教学由研究生助教或其他按小时记酬的讲师来完成。
资助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资金极为有限,这意味着那些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要自己想办法筹钱。一个最明显的办法就是代课,而且通常就是在他们读书的学校代课。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代课,因为这是领取大学奖学金的一个条件。他们有时候是按小时计酬,有时候被全职雇用,担任临时“研究生助教”或类似职位。
研究生助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科林·布莱逊估计,在总共7万名按小时计酬的讲师中,这些研究生助教只占15000名,“这跟在英国高校中从事教学的全职和部分兼职的拿工资员工人数相当,或者只是略微少一点儿”。[31]这些按小时计酬的讲师和其他合同制员工就是新自由主义化大学中朝不保夕的人员。这类员工数量在近几十年来大大增加,因为他们为教授日益增多的学生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方式。但对有些方面来说,这种形式所带来的代价都是高昂的。
按照布莱逊所做的研究或总结的说法,按小时计酬的讲师花在备课上的时间不算入工作时间,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培训或帮助,而且在所教课程的设计上没有发言权,事实上,他们在其他的院系决策上也没有发言权,因此,他们发现很难对这样占他们便宜的机构产生责任感。对从事研究的员工来说,虽然他们可以享受更大的工作满足感,但他们也苦于工作没有保障。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没法再享受在大型工业实验室里那种稳定、高薪的工作,而只能在大学里从事不稳定的工作。
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现象,这表现为女性大多是按小时计酬员工和研究人员,而处于大学等级制度上层的女性人数则在下降。[32]在2004-2005年度,女性占学术员工总数的40%,但只占教授和院系领导人数的15%,占高级讲师和研究者人数的29%。62.7%的女性员工从事全职工作,而相比之下,有76.7%的男性员工从事全职工作。[33]
在20世纪进程中,大学生的社会特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100年前,大学生大部分是贵族和中上阶层的男性后裔。在1900年,英国只有25000名大学生,在1924年有61000名,到1939年,达到了69000名。众所周知,牛津的本科生没有参加1926年5月的总罢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过去20年这两次高校扩招,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英国18岁年轻人进高校读书的比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低于3%,增加到1962-1963年的7.2%,1972-1973年达到14.2%,在1988-1989年则增加到了16.9%。[29](p.95)
尽管学生数量大幅增加,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来自体力劳动阶层的人发现自己仍然很难进入大学学习。由牛津大学诺非尔德(Nuffield)学院主持的一项关于英国二战后社会流动的研究,基于对1913年到1952年期间出生人员的访谈,发现在教育体系的每一级中,都是由那些被称为“服务阶层”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所把持:
在我们的研究所涵盖的40年中,中学机会不平等的状况一直都没有改变。某些中学教育具有选择性,40年中,服务阶层接受这种中学教育的机会大约是(体力)劳动阶层的3倍……40年来,有额外2%的劳动阶层孩子进入大学学习,相比之下,服务阶层的孩子有额外19%进入大学学习。[34](pp.205-206)
由于诺非尔德学院社会流动研究组(还有很多其他官方的研究)所采用的类别是基于收入和职业进行划分的,所以在某些方面会产生误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取决于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剥削——榨取直接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过程中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阶层包括所有那些被生活条件所迫,不得不接受剥削条款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劳动者。这意味着他们劳动不止是为了维持自己生计,还要给资本带来利润。这就要求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也不管他们技能如何,在工作中都要服从管理。[35]
如今,很多劳动者要接受大学教育,这是因为资本需要这种技术工人。在大量的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之上是一个人数较少的管理者阶层。他们负责监控其余的工人,以换取自身的自主权和物质特权,于是,这个管理者阶层本身就融入了资本家阶级当中。处于这些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之下的则是非技术性和低薪的体力劳动者,这些人的工作通常很不稳定,也正是这部分人的孩子最难进入大学学习。
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HEFCE)在2005年1月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英格兰18岁和19岁的年轻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占30%,在苏格兰,这一比例是38%。近年来最快的增长出现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而不是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年轻参与者”数量翻了一番,而从1994年到2000年,只增加了2%。此外,“根据居住地的不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广泛和明显的区别。居住在20%最发达地区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比居住在20%最落后地区的年轻人要高五六倍”。通过比较各议会选区的情况,该研究发现:
在4个参选率最低的议会选区——谢菲尔德的明朗(Brightside)选区、北诺丁汉选区、利兹市中心选区以及布里斯托南选区,其年轻人只有十分之一或者更少的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相比之下,在参选率最高的议会选区——肯辛顿和切尔西选区、西敏寺选区、谢菲尔德哈勒姆选区,以及伊斯伍德选区(苏格兰),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2](pp.9,10-11,41)
不需要是社会地理学专家你也知道,这两组选区分别包含了英国最富有以及最贫穷的地方。在普查区层次上更详细的分析表明:
这种情况是前后一致的——年轻人参选率低的地区,很多其他方面也处于劣势;相反,参选率高的地区在许多其他方面也占有优势。
在参选率低的地区,孩子们很可能住在当地政府的廉租房中。这些区域很多都属于全英格兰最贫困的地区,这里的孩子比起参选率高的区域中的孩子来活动空间小,家庭物品也少。从参选率的地区图可以看出,在离参选率低的区域最近的中学中,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在5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中得到A—C的成绩。与之相比,参选率高的区域通常与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取得上述成绩的学校距离很近,这些学校通常都是高等收费学校。在参选率低的区域,成年人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很低,或者接受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救济金,而且他们没有汽车,也不会去海外度假。这些人与那些参选率高的区域中的人相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这两类群体在一系列政治、文化和消费行为方式上有着很大差异。[2](pp.137-138)
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HEFCE)研究的发起人迈克尔·考沃指出,“如果英国所有区域的年轻人进入大学的比例,都能达到目前入学率前20%所在区域的标准,那么将会有额外的100万学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36]他的研究证实了更为人所知的不平等。优势和劣势是逐步积累的,换句话说,造成富者更富而穷者更穷的并不是某个单一因素,而是利于一批人但不利于其他人的一整套模式,包括孩子的母亲怀孕期间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饮食状况、居住条件、锻炼情况,也包括孩子一岁前是否有专人照料、阅读书籍和外出旅行的机会,还包括接受教育的质量和父母的帮助。当然,这套模式的基础还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情况。[37]
孩子的学校成绩——这对于他/她能否进入大学当然非常关键——在很多方面就是他/她在这一整套优势劣势模式中所处位置的体现。财政部的研究表明:
·如果一个父亲的收入是另一个父亲收入的两倍,那么他儿子比另一个父亲的儿子数学测验成绩平均高出5个百分点,阅读测试的成绩也高出2.7个百分点。
·他女儿则比另一个父亲的女儿数学测验和阅读测试的成绩都高出5个百分点。[38](p.32)
新工党政府充分意识到了高等教育入学上的不平等,我以上所引用的例证都来自工党政府自己的研究。而且,教育对布朗所追求的战略逐渐变得重要。布朗的战略是希望通过让个人更有效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来缩小不平等。“公平入学”是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号,其目标是要把18到30岁之间的人进入大学的比例,从目前的43%左右提高到2010年的50%。
一项研究的发起者指出,要实现这个目标“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出生率下降意味着达到大学入学年龄年轻人的数量在2010-2011年之后将会大幅下降。此外,大学入学率本来就较低的弱势社群出生率下降得尤其厉害,因此,事实上,这个群体的年轻人大学入学率会下降。[39]
不管这个分析正确与否,新工党的政策对它自己提出的增加大学入学机会的目标不利。这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布莱尔和布朗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热衷使得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继续保持。正如《金融时报》所指出的,尽管布朗努力将收入再分配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但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在工党执政9年之后,跟玛格丽特·撒切尔任期结束的时候相比,不平等程度要么相同,甚至更加严重……财政研究所(IFS)的迈克·布鲁尔说到,布朗先生不得不在再分配上花更多的钱达到了‘一无所获’”。[40]因此,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反映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上的优势劣势累积模式已经进一步确立。
其次,布莱尔政府通过廉价方式寻求高校扩招,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取消了生活费助学金,开始收学费,并不断提高学费,这就迫使学生自己筹措资金,从而背上日益沉重的债务。甚至在2006年秋季开始收取附加学费(大学一般都按一年3000英镑这一最高标准收取)之前,就有大量证据表明即将收费这一前景阻碍了来自贫困劳动阶层的年轻人进入大学。
在18岁和19岁的大学新生中,从公立学校和学院升上来的学生所占的比例从1999年到2003-2004年度略有增加,从85%增加到86.8%,但在2004-2005年度又减少到86.7%。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比例也有所下降,从2003-2004年度的28.6%减少到次年的28.2%。[41]从统计上来讲,这些变化幅度并不大,但有其他迹象表明,学生债务和学费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在2005年12月,申请英国大学的人数比前一年减少了5%。[42]在对7000名就读于公立学校12年级、并预计能在A-level考试中得到三个B或者更好成绩的学生中所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这些学生中的27%将因为大学收取更高的学费而更不可能进入大学学习。[43]同时,来自三个顶尖职业团体的申请者占到了罗素大学集团新招学生人数的73%。[44]
然而,尽管高等教育入学有着各种不平等,但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也更加多样化。大学每年有100万新生入学,其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于贫困阶层。这就意味着,作为一名大学生的经历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首先,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和未来的劳动者,他们有经济上的重要性。由于制造业的萎缩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大学已经成为很多英国城市经济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一项由副首相办公室委托的研究发现:
很多重要城市已经扭转了人口下降的趋势,并在效仿伦敦的成功之路,这其中的很大原因就是高等教育发展提升了劳动力水平,并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组成情况。
大量在曼彻斯特4所大学读书的学生在毕业之后留了下来,这明显改变了该城市的命运。
这些人又激活了住宅重建市场,并带动了当地基于知识的经济的发展。[45]
在一些地区,大量集中的学生进行消费所能带来的经济效应非常明显,比如曼彻斯特的牛津路,或者布里斯托的克利弗顿。不过,读者们也不应该在头脑中显现出一副有钱学生饮酒作乐的情景。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基于学费和学生贷款的学生金融体制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卫报》报导,在2003年11月公布的一项由政府委托伦敦南岸大学和政策研究进行的研究发现:
尽管贫困学生比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花了更多时间工作赚钱,更省吃俭用,但在毕业时还是都背上了平均一万镑的债务。从1998-1999年度到2002-2003年度期间,对处于大学最后一年的学生来说,其总学生债务从3465镑增加到平均8666镑,这增加了一倍还多。在2003年,有超过一半的本科生在毕业时预计将背负9673镑,或者更多的债务……全国学生联合会(NUS)主席曼迪·泰尔福特指责政府“将学生描绘成过着某种挥霍无度生活的形象”。她指出:“这项研究表明43%的学生处在贫困水平,这一比例是贫困家庭占总人口比例的两倍。”
报告总结指出:“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学生更有可能背上债务,并预计将在毕业时背负着最多的债务。”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由于有存款,并有来自其家庭“慷慨的经济资助”,所以避免了背上高额债务。[46]
另外,据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预计,收取附加学费将使学生债务增加为目前的三倍。根据《卫报》的报导:
研究还指出,那些残疾学生,以及无法从家庭得到资助的学生,将受到最大冲击……研究发现,学费已经直接被转化为债务:随着学费的增加,平均债务也随之同步增加。
此外,学费并没有引起学期期间打工的普遍增加。然而,对于那些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资助的学生来说,他们打工的时间确实增加了,这就使这些学生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研究也确实表明,收取学费将某些人拉到了同一平台上。那些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原来在学期期间很少打工,现在由于要交学费,他们很可能也要像其他学生那样,边学习边工作。[47]
最近一项由英国工会联盟(TUC)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合进行的研究表明,从1996年到2006年,通过打工赚钱来资助自己学业的全职学生的数量,从408880增加到680718,增加了54%。其中有十分之一是在做全职工作。根据这项研究的说法:
学生打工主要集中在零售业和酒店业,这是整个经济中工资最低的两个行业……
·在打工的全职学生中,在零售业工作的占40%,有将近50万人。
·有将近25万全职学生在酒店和餐馆打工,占打工学生总人数的21%。
·做兼职的男生平均工资,在零售业是每小时6.21镑,在酒店和餐馆是每小时5.70镑。对做兼职的女生来说就更低,分别只有5.98镑和5.51镑。
·从1996年到2006年,在酒店业打工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并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该行业中打工的男生人数自1996年春季以来增加了22.9%,而女生人数增加了45.8%,这一增加比例是男生增加比例的两倍。[48]
如果那些女生为资助其学业而跳艳舞是真事的话,那说明很多学生在从事着更为低级而危险的工作。而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学生融入了数量大得多的从事兼职、低薪和临时性工作而且朝不保夕的劳动力大军。这些劳动力,很多是来自外来移民,他们和那些知识经济理论所突出的高薪高技能职位一样,都是新自由主义化资本主义运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自从20世纪60年代高校扩招以来,学生就成为一个过渡性团体,他们在已处于其中的社会阶层以及将来可能的职业阶层之间漂浮不定。这种对自身未来的不确定使他们成为一个在政治方面摇摆不定的团体。[49]这种结构性的不稳定在今天还存在着。还有一些毋庸置疑的经济方面的好处在驱动学生进入大学:大学毕业生和获得“副学位”资格的人比没有学位人员的平均收入多50%。[4](p.59)
但是,这种“毕业生奖励”并没有使大部分毕业生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学毕业生能找到真正待遇好的职位——比如,伦敦金融城里面的高薪职位。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成为相对高薪高技能的白领工人。无论他们是进入公共部门还是进入私人部门,都要承担跟我们所谈到的在大学中工作一样的压力,都要求他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竞争力。学者自身的境况——这些人如今大多都有一个或两个研究生学位——非常清楚地表明,大学学历已经不再能确保在精英集团中获得一席之地了。
然而,这种模式整体上跟几十年前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学就成了培养白领工人的摇篮。然而,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大学扩招所达成的一点,就是迫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他们读书的时候就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在此期间所体验到的这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为他们毕业之后参加“自由主义世界中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抵制并非徒劳无功
在过去25年中,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化变革是残酷的,但同时也是零零碎碎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一点一滴逐步积累的过程。在每一个阶段,许多学者的反应已不再是抵制最新的不受欢迎的改变,而只是尽可能降低改变所造成的危害。这就导致了学者们在改变过程中采取合作态度,而这些改变的累积效果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对于帮助实现了那些他们非常厌恶的改变的很多学者来说,这种累积效果使他们垂头丧气。他们之所以采取了合作态度,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撒切尔夫人的名言——“别无选择”。因此,抵制新自由主义化“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有了这样一个假设,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加入到改革派,并成为目前管理大学的团体中的一员;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寻求各自的解决办法——要么提升,要么提早退休。
但选择还是有的——抵制并非毫无用处。自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1994年1月开始于墨西哥恰帕斯州,并于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以及2001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来,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世界社会论坛(这类运动的最广泛的聚集地)推广了这样一个口号——“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必向新自由化资本主义逻辑屈服。2002年11月于佛罗伦萨举行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扩展了运动的主题,使其包括了帝国主义和战争,并史无前例地号召将2003年2月15日定为全球抗议日,以反对即将到来的攻打伊拉克的战争。
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已经清晰可见,这尤其要归功于拉丁美洲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在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穷苦人民的支持下,利用国家的石油收入实行真正的社会改革,并公然反抗美国的霸权。在玻利维亚,2003年10月和2005年5-6月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穷人反抗运动推翻了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前两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当选为总统,进而寻求恢复国家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掌控,这些行业原来都已经被卖给了外国跨国公司。
发生在法国的反抗运动离我们更近,也更有意义。2006年3月和4月,在工会的支持下,法国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进行了一场盛大的抗议活动,成功地挫败了“首次雇佣合同”(CPE)法律草案,该法案将允许雇主在雇佣年龄不满26岁的年轻雇员的最初两年里随时解雇他们。这场反抗运动主要反对右翼政府试图强加给年轻劳动者更多不确定因素的观点,这场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1968年5-6月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联合反抗运动来说,这场反抗运动中学生与工人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斯塔西斯·库沃拉吉斯(Stathis Kouvelakis)写道:“这一次,学校和大学年轻人成了工人大家庭的一分子。”[50](p.5)
根据库沃拉吉斯的说法,这一变化反映了传统的关于中学及大学与工厂之间的功能划分已经消失。原来的观点认为,中学和大学是通过教育培养劳动力的地方,而工厂是生产商品的地方: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所具有的两种基本趋势作用下,这种功能划分逐渐变得模糊。这两种趋势是:一方面,中学和大学日益附属于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这种逻辑下,那些最大众化、最没有“竞争力”的学校变成了培训中心,并越来越多地依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出卖劳动力地位(这个地位一点儿也不令人羡慕)这样的逻辑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由于高中尤其是大学中打工赚钱的情况增多,中学和大学里的年轻人和年轻工人之间的差异在缩小。
某些行业或部门(快餐店、呼叫中心、百货商店和连锁超市)甚至专门雇用这一类工人。在法国,再加上强加到工人身上,尤其是18-26岁的年轻工人身上的不合正常比例的短期合同,虚伪的试用期以及失业期等,结果就造成了这部分劳动力的再次无产化。
这种转变加大了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差距——一小部分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可以进入中学、大学读书,而大部分年轻人要进工厂劳动。
当然,这场“伟大的变革”(与1968年的工人—学生运动相比)不仅使得跟工人的联合更容易,而且更是体现了其“有机”特色,这是“进行一场共同斗争”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不同运动结成同盟或者团体的方式。
这也解释了学生运动本身所采用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包括从上面的角度,使学生运动更靠近工人阶级斗争;对被看做是(也想成为)生产劳动力的厂房和工具的高中和大学进行封锁,中断其生产流程(讲课和考试)。[50](p.6)
学生运动的巨大推动力对工会领导人进行了制约,限制了他们的操纵空间,并且阻止了他们跟政府协商出一个方案从而可以保留“首次雇佣合同”(CPE)法案。哎呀,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在英国发生过。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库沃拉吉斯所描述的大量学生加入朝不保夕的劳动力队伍的趋势在英国也是愈演愈烈。发生在法国的学生运动对英国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这也鼓舞了欧洲其他地方的学生运动,在2006年5-6月,希腊大学生们在工会的支持下,占领了学校,从而迫使右翼政府推迟了他们将大学私有化的计划。
在英国,学术人员形成一种好斗的工联主义传统,从而导致了高校教师协会(AUT)与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教师协会(NATFHE)合并,组成新的大学和学院工会(UCU)。第一场考验发生在2006年春季,当时即将成立的工会发动了一场联合抵制活动,要求大学雇主履行他们和政府的承诺,从额外的学费收入中拿出钱来以扭转学术人员工资相对下降的趋势。
尽管大学管理层对老师们进行威吓,很多大学威胁说要降低那些参与抵制活动的老师的工资,而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大学那样做了,但是,联合抵制活动还是受到了大学教师们的大力支持。因为学术人员是服务工作者,其服务对象是直接的受益者,因此,采取罢工行动一直比较困难。停止教学和阅卷是罢工最有效的形式,但这直接伤害到了学生,因为这样会影响到他们接受教育,甚至会影响到他们取得学位。这并不是要反对教师罢工。老师们应该采取快速有效的行动——全体罢工或者抵制评估运动,从而可以在减少对学生伤害的同时,向雇主施加最大压力,并使其接受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学生们对抵制运动的反应是复杂的。全国学生联合会(NUS)负责人对抵制运动持支持态度,但是他们也受到一些来自于反对抵制运动的地区学联的压力。这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学联的领导层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运动保护学生利益,比如关于附加学费的问题。由于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学生会被那种将他们作为个体消费者的观点所吸引,从而寻求针对教师工会行使他们的权力。
第二个问题是,库沃拉吉斯所强调的社会变革还有另一面。学生是一个由不同社会成分组成的群体。虽然大多数学生会从事技能要求或高或低的白领工作,但有一些来自特权阶层的学生早就确保了他们能前程似锦。其他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仍然非常渴望得到一小部分精英才能获得的高薪工作,尤其是伦敦金融城里的工作。那些有希望继承或者爬到社会阶级结构上层的学生是不可能对这种集体行动太友好的,因为这些集体行动的目的就是要纠正他们希望从中获益的不平等机制。
2006年的评估抵制运动最后变成了一场老鹰捉小鸡的游戏:看谁先眨巴眼睛——是工会还是大学雇主。不幸的是,当时即将要成为大学和学院工会(UCU)的机构负责人先眨了眼睛。他们最终没有遵守对成员们所作的承诺,即在进行投票之前不会放弃行动。他们终止了抵抗运动,接受了一个几天前被他们拒绝后稍加改动的新方案。
工会官员们辩称这种屈服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认为抵制行动当时已经开始瓦解了(虽然他们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抵制行动继续下去的话,很多大学管理者将会退出全国性的工资谈判。毫无疑问,地方谈判确实是一个威胁,但只有一样东西能阻止这种威胁,那就是表现出工会的能力,而不是表现出软弱。
尽管如此,抵制行动的力度还是表现了很多学者对他们工会的忠诚度。或许,这在一些老牌大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年轻的合同制员工给当地高校教师协会(AUT)增添了活力,使它们事实上变成了工会的分支机构。因此,这次抵制运动同时也体现了大学和学院工会所具有的潜力,因为它要求合并后的工会中的左派要更有效地组织起来以担负领导责任。
对大学教师的工会来说,像这种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教师协会以及高校教师协会通常是进步性的政策与这些协会的官方人员在抵制活动中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新鲜事或者个案。工会的全职官方人员们试图建立一个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进行斡旋的独特社会群体。他们试图通过谈判改善对工人的剥削状况,而不是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以最终消除这种剥削。因此,虽然选举一个尽可能好的工会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层人员绝对不应该依赖他们,而应该自己组织起来。
新成立的大学和学院工会中的左派(UCU Left)在2006年6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它们尽力争取建立强大的基层组织,从而使这些组织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依赖工会的全职官员而采取行动。这也需要更宽广的政治视野。我们已经看到,真正拖累这么多大学——和其他工作场所——工作者的是一种信念,即除了新自由化资本主义以外他们别无选择。要求实现另一种全球化的运动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挑战了这一信念,它指出,在一个世界里市场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学里的左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全球性抵制新自由主义和战争运动的一部分。
这就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行动。欧洲社会论坛已经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让来自全欧洲的教育活动家能当面交流看法。但是,相比于大学学者来说,这种方式对教师和他们的工会显得有些超前。不过,既然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为什么不能有另外一种大学呢?
如今,大学成了各种不同社会功能的大杂烩,主要包括:
·个人的自我发展
·复杂的、在社会上有用的技能传授
·“纯”研究——为知识本身而进行的研究
·商业性和军事性研究的开展
·帮助创造一个内聚性的统治阶层
·对社会的批判性反思
当前大学重组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直接服从于新自由化资本主义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终身学习、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国务大臣比尔·拉梅尔可以不必理会在2005年大学录取中一些专业——比如:哲学、历史、古典文学和美术——申请者的减少。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他解释说:“学生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可以使他们职业受益的专业。”[51]
不过,没有什么特别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上述那些社会功能要由一个机构来承担——事实上,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过。很多在过去几百年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比如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不在大学工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辉煌时期,不过他是在日内瓦专利局做职员的时候写出了那些彻底改变了物理学的文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才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发源地,很多人认为这就鼓励了以学术人员为读者对象的深奥的理论性论文的创作。[52]
我们当然应该保护现有大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使其免受那些对它造成破坏的威胁,这些威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化的改革。比如,考虑到那些顾左右而言他的公司媒体的广泛影响力,大学继续提供一个批判思想产生的知识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批判性讨论的其中一个主题,应该是大学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活动,比如寻求自我发展、获得新技能以及学术研究,不一定要在同一个机构中进行,也不必非要限定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完成,这个特定阶段通常是早期成年期——这是有关“终身学习”的官方论调中的真实成分。
大学管理也绝对没必要采用目前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方式,其中管理者和高级学术研究人员处在等级制度的上层。20世纪60-70年代学生运动所要求的大学民主制——让学生以及所有的大学员工都能参与决策——到今天仍不失其相关性。
但任何实际的改善大学处境并使其民主化的尝试都会跟政府意图发生冲突。在大企业的支持下,政府试图利用高等教育保持竞争和利益的优先性。比如,这种优先性无法容忍通过累进税制资助实现将资源从富人分到穷人手里的大规模再分配,因为那样将需要从早期教育阶段就实现入学机会的真正公平。
新自由主义所做的就是将自己分离出来实现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逻辑。正如我们在大学中所看到的情况那样,这是一种竞争和利益的逻辑。要挑战这个逻辑就意味着要追求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由不同优先性支配的世界——比如社会正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真正的民主。[53]要维持并发展目前大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就不能从更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孤立出来。
参考文献:
[1] www.hesa.ac.uk/holisdocs/pubinfo/student/institution405.html [Z] .
[2] HEFCE.Young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Z] . www.hefce.ac.uk,January 2005.
[3] Peter Hitchens. Why Does Everyone Find it So Hard to Understand the Tories?[Z] . hitchensblog.mailonsunday.co.uk,2006-05-17.
[4]、[4a]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Z] . www.dfes.gov.uk,January 2003.
[5] David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6] G. Dumenil and D. Levy. Neoliberal Income Trends [J] . New Left Review,2004(11/30).
[7] Mike Brewer et 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Britain: 2006 [R] . 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 www.ifs.org.uk, March 2006.
[8]、[8a] C. Leadbeater. Living on Thin Air [M] .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2005.
[9] T.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M] . London: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
[10] A. Callinicos. Against the Third Way [M] .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1. &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M] .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3.
[11] B. Benoit and R. Milne. Germany's Exporters are Beating the World [N] . Financial Times,2006-05-18.
[12] J. Johnson. Asia Faces Jobs Crisis that Could Hit Growth [N] . Financial Times,2006-04-27.
[13] R. Brenner. Towards the Precipice [Z] . London Review of Books,6 February 2003-02-06. & R.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M] . London: W. W. Norton Company,2002.
[14]、[14a]、[14b] H. M. Treasury.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 2004-2014 [R] . www.hm-treasury.gov.uk,July 2004.
[15]、[15a]、[15b]、[15c]、[15d] Lambert Review of Business-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Final Report [R] . www.lambertreview.org.uk,December 2003.
[16] A. Cockburn and R. Blackburn. Student Power [M] .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69.
[17] AUT. The Pay Campaign in Brief A [Z] . www.aut.org.uk/paybacktime.
[18] AUT. The Academic Pay Shorfall 1981-2003 [Z] . www.aut.org.uk.
[19] H. M. Treasury.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 2004-2014: Next Steps [R] . www.hm-treasury.gov.uk, March 2006.
[20] HEFCE. RAE 200: Guidance on Submissions [Z] . www.rae.ac.uk, June 2005.
[21] House of Commons 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Fifth Report of Session 2002-3 [R] . www.dfes.gov.uk,2003-07-10.
[22] D. Macleod. Overseas Student Numbers Rise [N] . Guardian,2006-03-13.
[23] D. Macleod. International Rescue [N] . Guardian,2006-04-18.
[24] M. Taylor. AUT Calls for Inquiry into ice-Chancellors' Pay [N] . Guardian,2006-03-09.
[25] Third Stream as Second Mission [Z] . www.hefce.ac.uk, 2006-05-18.
[26] J. Boone. Academics Learn to License Inventions [N] .Financial Times 2006-07-26.
[27] J. Boone. University Company Sells Stake for £25 Million [N] . Financial Times, 2006-07-21.
[28] J. Boone. Most Colleges 'Set to Sign Technology Transfer Deals' [N] . Financial Times,2006-08-01.
[29] A. H. Halsey. Decline of Donnish Domination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0] See C. Bryson. What about the Workers? The Expla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Work [J] .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2004(35).
[31] C. Bryson. Hiring Lecturers by the Hour [Z] . NATFHE, www.natfhe.org.uk, April 2005.
[32] C. Bryson. The Consequences for Women i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of the Widespread Use of Fixed Term Contracts [J] . Gender, Work and Organisation,2004(11).
[33] C. Johnston. Figures Show Rise in Part-Time Academics Staff [N] . Guardian,2006-02-20.
[34] A. H. Halsey et al.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35] See A. Callinicos and C. Harman. The Changing Working Class [M] . London: Bookmarks,1987.
[36] D. Macleod. Equality 'Would Double University Admissions' [N] . Guardian, 2005-01-19.
[37] B. Barry. Why Social Justice Matters [M] . Cambridge: Polity,2005.
[38] H. M. Treasury. Trackling Poverty and Extending Opportunity [Z] . www.hm-treasury.gov.uk,March 1999.
[39]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till 2020 [Z] . www.hepi.ac.uk,21 March 2006.
[40] C. Giles and J. Wilson. State Largesse Brings Hope but Little Change [N] . Financial Times,2006-09-19.
[41] A. Smith. Government Failing to Widen University Access, Figures Show [N] . Guardian,2006-07-20.
[42] D. Macleod. Fee Concern over Fall in University Applications [N] . Guardian,2005-12-15.
[43] M. Taylor. Fee Deter State School Pupils from University [N] . Guardian,2006-06-22.
[44] R. Garner and B. Russell. Private School Stranglehold on Top Jobs [N] . Independent,2006-06-15.
[45] M. Green. Universities and Local Power Vital to Recovery of Leading Cities, Says Study [N] . Financial Times,2006-03-08.
[46] L. Ward. Poor Students Shoulder Debt for Learning [N] . Guardian,2005-01-28.
[47] Fees to Triple Student Debt, Says Study [N] . Guardian,2005-01-28.
[48] TUV/NUS. All Work and No Pay [Z] . www.tuc.org.uk,2006.
[49] C. Harman et al. Education, Capitalism and the Student Revolt [M] . Lond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1969. & G. Stedman Jones. The Meaning of the Student Revolt [A] . A. Cockburn and R. Blackburn. Student Power [C] .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69. & A. Callinicos and S. Turner. The Student Movement Today [J] . International Socialism,1975(1.75).
[50] S. Kouvelakis. France: From Revolt to Alternative [Z] .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endency Discussion Bulletin, www.istendency.net, No.8,July 2006.
[51] Trend to Drop Philosophy No Bad Things, Says Rammell [N] . Guardian,2006-02-15.
[52] R. Jacoby. The Last Intellectuals [M] . New York: Basic Books,1987.
[53] A. Callinicos. Alternatives to Neoliberalism [J] . Socialist Review, Jul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