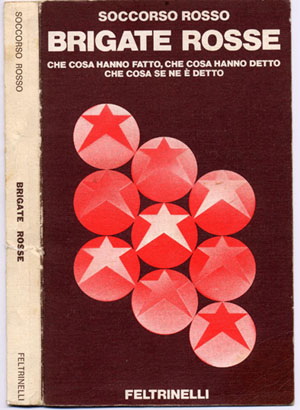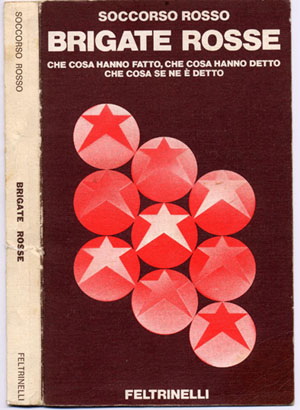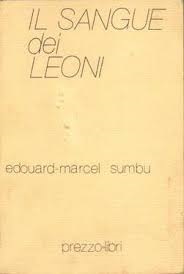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八章 武装斗争与工人自主
“武斗”倾向的来源
1976年,匿名作者在《红色旅》(Brigate Rosse)一书的封面上写道:“于是,对红色旅的恐怖成为了给激进反对派定罪的保证,意大利得以效仿德国制定严酷的镇压法律、抹去所有防范与镇压的界限……”另一处提到:“从这个意义(去伪存真)上讲,赤色济难会的书是一次正直的尝试。此时此刻,出版本书是希望告诉公众不为人知的故事,这应当成为现代作者的特点。”[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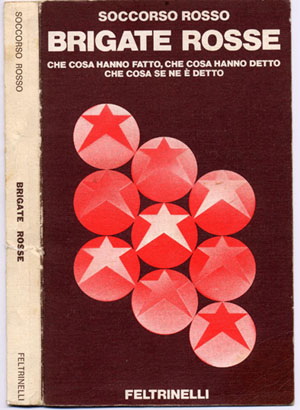
红色救助会《红色旅》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
编者在书的注释中更详细地阐明了他的想法。他驳斥了所有对红色旅“纯属一窝奸细和特务”的指控,认为他们是在为一项“使得整代积极分子遭受迫害的事业”而战。以下是对问题根源的简要分析(由弗朗切斯科·奇阿法洛尼〔Francesco Ciafaloni〕写于《皮亚察琴科笔记》):“1969—72年间(后来也是),不少的年轻人,也就是工厂和学校中斗争的主角……突然之间,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彻底转变了……”但接着“从旧的立场到新的立场,还没有一个自觉的、经过讨论的与理性的过渡,来让群众层面的思想得以连贯传承。大多数人重建了队伍。他们仅仅是发觉了,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并意识到自己没有对这一代价做好准备。一些人没有走出矛盾。还有一些人则将这条路走到了最后……”[2]
这些话是在议会外团体瓦解的极端时期写下的,与此同时,工厂也进行了广泛而专横的重组(补助资金管理局[3]与“政治”解雇等等),政府和议会也制订野蛮的立法,被称为“紧急时期”的历史拉开帷幕。
这本关于红色旅的书很快售罄,从未再版。它与亚历山德罗·西洛(Alessandro Silo)的《握紧手中枪》(Mai piú senza fucile)是少有的不是为了欺骗——如果不是粗俗的诽谤——而是试图寻找意大利武装斗争现象根源的尝试。

亚历山德罗·西洛《握紧手中枪》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红色旅和地下暴力武装行动一直都是热门话题。国家的“紧张战略”不仅煽动了资产阶级报刊,也让运动内部产生分歧。虽然民主反信息公报和运动站在同一立场,但它始终将红色旅斥责为“奸细”。《宣言》报多年来也认为红色旅是在煽风点火,还说他们是国家的同谋。
实际上,红色旅在刚成立的时候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黑暗”。可以说,其诞生就是一个“对运动来说是光明,对权力来说是黑暗”的运动理论的绝佳例证。
红色旅最初在工厂中开展活动,尤其是在米兰的倍耐力和西门子。刚开始它们没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它们与其他政治力量发起的行动,或者工人类似的自发行为混在了一起。需要强调一点,在“火热之秋”和1970年间,殴打工头、砸坏工头或管理层的车,以及厂内反抗权力的行动,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不断斗争”在它的半月刊中,提及了当时工厂的气氛:
每次行动、示威和封锁货物之后……各部门都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法庭:那些有能力但是没有参加(行动)的人都从工厂中被揪了出来。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在一个车间部门里,听说有七个人偷偷在星期天工作,他们是四名工人和三名领班。工人进行了讨论,工贼都被“停职”了:工人两天,领班三天。三天是因为他们是工头,也因为在讨论时,他们其中一位不尊重工人,说这关他屁事……这不仅是在捍卫团结:工人学会了行使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进行管理。
[4]
这样的气氛下,红色旅开始活动。红色旅的传奇始于1970年9月17日,第一场行动以五角星为记号,他们点燃了西门子经理莱昂尼(Leoni)的车。他们没有散发任何小册子。但晚上在西门子工程师吉奥尔基·维拉(Giorgio Villa)的法拉利雨刮器上,留下了手写便条,语气介于嘲讽和威胁之间:“这辆法拉利还能开多久?我们决定要砸烂它之前。红色旅。”[5]
在这些“典型”行动之前,红色旅在米兰洛伦特乔的工人阶级街区,面对一群好奇又惊讶的听众开了一场集会,还在西门子门口分发了小册子。

《无产阶级左派》的通讯
1970年10月20日,《无产阶级左派》(Sinistra Proletaria)在斗争通讯中报道了红色旅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刻:
红色之秋已经开始
即将来临的秋天……是与政权对抗的一场关键战斗的尾声……为了反对剥削我们的制度,反对老板的法律和正义,斗争的无产阶级中最自觉和最坚决的部分,已经开始为建立新的法律、新的权力,为了建立它的组织而战斗。其中一例就是特伦多伊格尼斯的工人,他们
绑架并扣押了故意捅伤两名工人的法西斯挑衅者。他们还
占领和保卫房屋,这是有地方住的唯一方法……
工人自主组织(红色旅)的出现,标志着无产阶级开始了最初的自我组织,他们与老板及其走狗斗争时,也采用了后者反对工人阶级的同种手段:就像在西门子一样,直接、隐蔽又针对性的手段。
让我们组织起人民群众的抵抗……
是时候让我们在火线上组织起来,在斗争中确立新的革命实践:人民游击战的策略。是时候推动全面对抗,为了:
—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确立“没有武装力量就没有政治权力”的斗争原则;
—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左翼的
游击活动,在抗争和武装斗争中启发教育;
—揭露用来瓦解阶级团结的镇压机关与压迫组织
[6]。
那么这个“无产阶级左派”是什么?它是一本在1970年出了两版的杂志。《无产阶级左派》的刊物出版前,还出了几本小册子,标有“城市政治集团出版”的字样。正如我们所见,在1968—69年,米兰的基层统一委员会经过讨论后,成立了“城市政治集团”。这一组织的诞生,是为了将工厂的行动扩展到社会,克服当时工厂斗争与学生—社会斗争的分离。“集团”在一篇文章中(1970年1月)提出了需要新的组织形式:
我们必须提出这个具体问题。哪一层面的组织,在今天是可能且必要的?……
基层统一委员会、学习会(Gruppo di Studio,GDS)和基层学生运动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通过自主决策与自我管理的斗争,让无产阶级自主运动重生。这类斗争基本在工厂和学校中开展,也就是说,它们在制度内部发挥作用……当斗争蔓延开来,获得许多政治自主性质的那一刻……它们将不再发挥政治作用,而是被自身产生的斗争所克服。
如今,无产阶级自主性的发展,意味着克服孤立的斗争与组织。这只有通过与运动的“保守”倾向斗争才能实现,并以自主组织的形式——委员会、学习会与学运——克服它。
[7]
基层统一委员会内部爆发的“群众路线”和“党派路线”之争,从根本上讲,是基层和革命团体——其试图将委员会的角色重新定位在政党制度之内——两种倾向之间的论战,下述文章具体地表现了这一点:
斗争的社会层面需要社会的基层组织……自然,这不是要让基层组织一步成为提供领导的组织……而是要建立在政治上同质化的组织,以此干预大城市的社会斗争。
克服工人主义与学生主义……不能通过工人和学生自发的、零星的与非政治的联合来实现……而是要在复杂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建立组织的核心。
[8]
尤其在米兰,“集团”迅速成为一个群众组织,遍布数十家工厂和学校。尽管分属不同组织,“工人力量”的一些成员明显对它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同情和兴趣,因为它是工人自主组织的一个模范。
以下是1969年底,“集团”在基亚瓦里大会上的文件,这场会议是在国家恐怖主义的背景下举办的。会议上主要提出了组织、政治路线与暴力的问题。毫无疑问,不管是1969年间极为严厉的镇压气氛,还是在火热之秋中,工人自发的大规模“暴力”留下的印象,又或者两大政治小组(“不断斗争”与“工人力量”)在斗争中的战略分析,都对这份文件的起草与问题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雷纳托·库尔乔[9]和其他积极分子为核心的“城市政治集团”吸取了特伦多“反大学”(la Universidad Negativa)的经验,他们批判了“不断斗争”与“工人力量”的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从特伦多经验中得出的长期斗争的概念:
阶级斗争分为三个要素:目标、斗争方式与组织。工人阶级在统一的目标下推动斗争,而组织又是斗争的结果……
斗争表达了统一的目标和激进的形式,所以应当考虑到它是促进还是阻碍的因素。组织在后来才出现,因为需要“保存”斗争在思想层面上取得的成果……
因此,在长期“阵地战”的假说中,工人阶级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得到了力量。
我们分析的是“不断斗争”和“工人权力”的立场。它们认为,自主组织是发展斗争的先决条件。自主被理解为相对工会和党的“独立”……
自主的发展被理解为与传统组织相对立的组织之发展。我们认为这一自主的观念是肤浅和局限的,按照这一观念,自主仅仅是发展斗争的工具和条件……在工人运动内部,对于1968—69年的群众自主斗争有两种基本态度:
—不理解进行决裂的必要,试图恢复和发掘“政治复辟”的潜力。
—尽管来自各派别,但都将无产阶级的自主作为今后开展政治工作的出发点……
站在后一立场的我们,坚持这是唯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在欧洲大城市发展革命斗争的立场。
因为事实如此。与其立即取胜赢得一切(从“说”到“做”都很简单),不如在长期斗争中成长,利用运动中遇到的强大障碍,从群众的自发运动飞跃到有组织的革命运动。
[10]
1970年间,“集团”正好得到了在斗争和当前形势下进行教育与联合的工具,它就是《无产阶级左派》。许多工厂中的斗争、在米兰麦克马洪大街和加拉腊特西社区发生的一些大型占屋运动,以及后来在“夺取交通”和“不花钱坐公交”的口号下开展的交通斗争运动,都是以它的名义来领导和声援的。
在韵律和内容上,这些口号承接了“不断斗争”在运动中——《无产阶级左派》也加入了——提出的“夺取城市”和“不交房租”。
此外,“集团”还对技术人员和学生工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从而在工厂和社会斗争的扩展上得到了最强大的助力。
“技术人员”的问题,是由“集团”的成员和工人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1968年11月,战斗中的米兰举办了一场科学院校的全国会议,会议对正在进行的技术结构调整、技术人员在新资本主义下的作用等等,进行了重要的分析。“工人力量”的弗兰科·皮佩尔诺[11]在长篇报告中,还分析了“核裂变”与“核聚变”的关系,超前提出了这个多年后“流行”的问题。但是,不仅是革命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进行中的阶级对抗中的位置,使得技术人员的走向变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1969年初的全国技术人员罢工后,“城市政治集团”参与斗争,它得到了倍耐力委员会与西门子学习会的技术人员与职员的大力支持。同样在这一政治理论下,IBM学习会成立了,这家公司与奥利维蒂(Olivetti)共同跻身于生产技术的前沿。
“集团”—无产阶级左派在统一工厂与社会斗争的战略下,与“工人力量”和“不断斗争”在住房和交通问题上建立了广泛的同盟,它吸取了基层统一委员会的创造性经验成果(委员会里的学生工对结盟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始系统性地介入职业技术学院,那里的学生工人数最多,也是技术人员未来就业问题最突出的地方。
米兰是意大利学生工最集中的地方(1970年约有八万学生)。由于这是一座工业城市,学生工的骚动在学校和工厂斗争之间架起了一座天然桥梁。在1970年的头几个月里,学生工的斗争和运动完全由“城市政治集团”掌握,后者对学生工这一社会角色的职能进行了最全面的理论分析。学生工运动[12]汇集了来自各地(倍耐力委员会的成员、特伦多的学生等等)的积极分子,它在费尔特里内利技术学院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了典范。在集团与学工运的共同分析中,夜校被定义为工厂:
夜校是一种生产组织……它将人像货物一样生产。停学、休学、施压和开除……用这些方式,夜间工厂从生产过程中剔除了生产材料中的最杰出部分。因此,“筛选”无非是对产品的“质量控制”。这个制度根据自己对工人的需求,开办或关闭夜校。
但夜校同样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功能:质量控制的前提是,生产对于制度本身是“同质”的,于是老板需要建立“无产群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共识”。简而言之,在工厂中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上的剥削,在学校里则表现为政治思想上的压迫。
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是一项真正的工作,因为它生产着一件实实在在的东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劳动力。夜校等于四小时的加班。有人表示反对:法律要求给夜班付钱。但这是什么法律?就和学校一样,法律也是属于老板的。
斗争是被剥削者的法律。
我们要奉行和实践的法律只有一件:反对剥削的不断斗争,而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企图使这种剥削成为正当的,因而也是合法的。
[13]
红色旅的诞生
1969年秋季与1970年春季的斗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引起了政权的真正危机。老板们和国家秘密机关曾想用扩大工会合法性、“炸弹战略”和暴力镇压来遏制工人与社会冲突,现在不得不寻找新的办法。阿涅利甚至预言了“工会和雇主必须共同来捍卫某些目标,甚至有可能是捍卫政治权力本身……”
在《劳动法》和工厂委员会上让步,也是想在新的游戏规则内,以新的代表形式来遏制运动。但是,工人自主行动无视了任何的游戏规则,它还采用了新的代表机构,几乎始终保持着自主性,并且独立于工会中央。
“工人力量”、“不断斗争”和集团(现在是《无产阶级左派》)对国家机器可能转向反动专制的分析变得越来越准确,这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建立自卫组织与(不仅是防御性,而且也用于进攻的)军事—政治组织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红色旅的标志
出版商詹加科莫·费尔特里内利在六九年夏天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表达了他对“政变”危险的担忧。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是:《六九之夏,意大利政变、彻底且专制的右转之迫在眉睫威胁》[14],它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附录中还引用了希腊小说家瓦西里斯·瓦西里科斯[15]的《希腊也不可能》[16],小说讲的是一场政变,“上校们”在这场政变中被美国特务密谋推上台,血腥镇压了国内运动。
但导致运动出现武装组织的,不仅是对政变的担忧。在国家恐怖主义下,资产阶级挑起的军事冲突成为了诸多分析的主题,有力地推动了这些理论思想。关于拉美城市游击队(尤其是乌拉圭的图帕马罗[17])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调节中心的大城市的话题被讨论得越来越多。基亚瓦里的“城市政治集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社会层面的斗争是斗争的高潮:普遍反抗压迫的斗争正是革命之时……资产阶级选择了非法手段。对它的回应只有在大城市进行革命长征。
它应当从此刻此处开始。……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大城市地区开展革命的意义,尚未被充分理解。过去农村地区的革命理论已经不适用了……
一:在北美和欧洲的大城市地区,步入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斗争的主要是为了创造主观条件……
二:体制与上层建筑越来越趋于一致,这导致今天的革命与全球化、政治及“文化”同进退。这意味着,群众运动与革命组织的关系应当彻底转变,组织原则亦然。
今天,城市是体制的心脏,是政治—经济剥削的中心,是资本发展的结晶,是推动无产阶级融合之处。但是,它也是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在此,矛盾得以最尖锐地表现,晚期资本主义的组织混乱也表现得最明显。
必须对这里,对体制的心脏发起打击。
必须要让越来越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敌人,在城市中失去安全感。必须让敌人的每一举动都能被掌握,让所有不公都能得到伸张,让所有政治与经济的阴谋都能被揭露。
[18]
另一方面,乌托邦的武装斗争似乎遍布了世界各地: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在拉美大城市中,在斗争愈发艰苦的巴勒斯坦,尤其是在欧洲的心脏地带,红军派[19]在德国极高效地开展活动。1970年10月出版的《无产阶级左派》最后一期写道:
游击队已经走出了最初的阶段……它不再仅仅作为引爆器……已经历史性地克服了旧的起义战略……渗透到大城市中,以共同的斗争形式和战略将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资本用它的反革命武装计划统一了世界,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游击战下统一了起来。
意大利和欧洲也不是历史的例外。[20]
1971年2月,《无产阶级左派》的短暂生涯告终。创办它的同志们在短短接个月之内就退出了合法活动,自然是转入了地下。
另一方面,其他小组的分析似乎也表明,需要让对抗更进一步。尤其是和“工人力量”同样广泛分布在都灵工厂中的“不断斗争”,它更倾向用“无产阶级正义”来对付资产阶级,并有力地提出了工人反击的问题。这一时期,在游行中传唱的斗争歌曲也诞生了,它既能给游行者带来节拍,又能彰显斗争的意义:
菲亚特之歌
A·班德利(A. Bandelli)
雇主先生这次轮到你
事情的结果肯定会很糟糕
我们厌倦了等待
等待你把我们杀了
我们继续工作
工会来告诉我们
要空谈些什么
但从不谈论斗争
雇主先生我们醒了
这次我们要开战
这次我们要战斗
我们已经决定
看到工贼如何溜走
听到车间的沉默
也许明天你只能听到
炮火的轰鸣!
雇主先生这次轮到你
事情的结果肯定会很糟糕
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想谈判
你必须意识到这是没可能的
这次你不能再用
五个里拉来收买我们
如果你给我们十个,那我们要百个
如果你给我们百个,那我们要千个
雇主先生别欺骗我们
用你发明的代表
你的计划化为泡影了
我们斗争反对你
反对专业类别
我们想废除它们所以
区别已经结束了
生产线上我们都一样!
雇主先生这次
我们学会了斗争
在米拉费奥里
也在整个意大利
当我们走上街头
你等待的是一场葬礼
但想让我们睡觉的人
他做的不太好
我们真的见到那么多
罗马盾和警棍
但也看到那么多手
开始寻找石头
整个都灵的无产者
毫不畏惧地
回击警察的暴力
必须要来一场艰苦的战斗!
对官僚和老板说不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一切!
斗争在米拉费奥里继续着!
共产主义也将胜利!
对官僚和老板说不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一切!
斗争在厂内厂外继续着!
共产主义也将胜利!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皮诺·马西[21]与皮耶罗·尼西姆[22]
全世界都在爆炸
从安哥拉到巴勒斯坦,
拉丁美洲在战斗,
在印度支那,武装斗争已经胜利;
全世界的人民开始觉醒
走上街头,实施正义的暴力。
那么,同志,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尼克松、阿格纽[23]和麦克纳马拉[24]的美国
在黑豹那儿挨了教训;
人民可不喜欢凝固汽油弹的文明,
只要老板存在,和平就永无可能;
老板的和平是方便老板的,
和平共处是骗局,只为安抚人心。
那么,同志,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西班牙和波兰的工人
教导我们:这斗争从未停止
反对联合起来的老板,反对资本主义,
就算它戴上社会主义假面具。
罢工的波兰工人
在游行中高呼:“盖世太保警察!”
他们喊:“哥穆尔卡[25]不会有好下场!”
他们前进,高唱着《国际歌》。
那么,同志,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欧洲群众也不再袖手旁观
斗争无处不在,停也停不下,
处处都是街垒:从布尔戈斯到什切青,
还有我们这儿,从阿沃拉到都灵
奥尔格索沃到马尔盖腊、巴蒂帕利亚到雷焦
艰苦的斗争在推进,统治者要完蛋啦。
那么,同志,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
注:这首歌的曲调是60年代由巴里·麦圭尔(Barry McGuire)唱红的美国著名反战歌曲《毁灭前夕》(Eve of Destruction)。词曲作者是P.F.斯隆(P.F.Sloan)。
→ 《菲亚特之歌》视频版
→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视频版
在1970年秋天开始活动的红色旅,刚开始没有获得什么反响。直到1971年1月拉伊纳特试跑道纵火案,他们才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1971年1月25日晚上,他们将八枚燃烧弹放置在试跑道上(用来测试倍耐力的轮胎)停放的汽车底下。三辆完全被毁,其他五辆由于生产缺陷(主要是受潮)仍然完好无损。在跑道入口留下的一张纸上写着:DELLA TORRE-CONTRATTO TAGLI DELLA PAGA-MACMAHON-BRIGATE ROSSE。(德拉·托雷—合同—麦克马洪—红色旅。德拉·托雷是倍耐力公司一名被解雇的工人,麦克马洪是米兰市区的名字,当时发生了占屋运动。)
口信上提到了倍耐力的一名工人,他在大规模占屋运动和厂内斗争期间被解雇。
《晚邮报》对这件事相当重视,为此撰写了五栏文章,(也许是第一次)称红色旅为“幽灵般的议会外团体”。
之前一直对红色旅的活动缄口不言的共产党和《团结报》,在专栏的一篇短文中谴责和贬低了这件事:“不管是谁(搞了这起袭击),就算用革命的辞藻躲在匿名小册子后面,这也是不被倍耐力工人接受的,它在公众眼里就是一连串的破坏行为。”[26]
根据意共的声明,工人必须首先摆脱这些奸细:“发生这些行为时,工人必须最先采取行动,以最理想的、与其行为本质相对应的[27]方式把他们从队伍中间赶走。”[28]共产党明确表明要以暴力维持秩序, 再结合工会之前把红色旅称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寻衅枪手”的声明,这一态度就更加明显了。
另外,“不断斗争”也作出了消极的回应,将该行动定义为“典型”非群众性的挑衅行为。它在声明中写道:“正因为无产阶级群众无需理解暴力是必须的,这些‘典型’行为都是不必要的……群众的武装组织没能建立,就是因为一些团体在搞武装活动……(武装活动应当)建立在群众的稳定与自主的政治组织基础之上。”[29]
不管怎么样,红色旅的行动(尤其是在米兰)继续成倍增长,在《无产阶级左派》停刊后,《新抵抗运动》(Nuova Resistenza)是捍卫红色旅最坚定的报纸。它的名称取自无产阶级左派(法)[30]的文章,后者是一个在被宣布非法前就在地下斗争的,法国五月风暴中最激进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左派(法)的纲领文件表明了它与《无产阶级左派》实践的紧密联系:“我们的方针叫做:‘新抵抗运动:游击队员的人民暴力斗争’……打游击的时候到了。”
《新抵抗运动》于1971年出版。在报纸的名字下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旁边是《无产阶级左派》的标志:交错的镰刀、锤子和步枪。这份自称“新抵抗运动的共产主义报纸”最终在共产党的基层产生了吸引力。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在五十年代还是后来,前游击队员和党员从未放弃过对抵抗运动的有限成就进行强烈批判,即应当继续进行广泛的阶级对抗,直到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这一目标,法西斯倒台后,还有许多游击队员没有交出武器。五十年代里,宪兵和警察在山区和一些工厂的地下室里,搜出了成千上百的步枪、左轮手枪和迫击炮。这些前游击队员自然已经带上了神话与幻想的色彩,但毫无疑问,至少在1960年7月,他们又重新武装起来走上街头了。达尼洛·蒙塔尔迪在他的《基层政治积极分子》(I militanti polítici di base)中,将这一潮流称为“低声”(sottovoce),这是用工人俚语玩的文字游戏。其实“低声”指的是一种小酒(grappino),它在八点前不让卖,工人早上进厂前就喝它。


1971年4月及5月的《新抵抗运动》报
显然,基层党员受到它的影响,有了新的想法,而共产党与新资本主义以及中左翼政府的“合作”路线——它不断受到指责——也推动了这一过程。
战后初期在米兰和意大利北部活动的游击组织红色机动队(见上文)的故事也被口口相传。在北方各地也出现过和红机一样的游击队,尤其是在利古里亚和埃米利亚,这些地方拥有最强烈的共产党和游击队传统。而在雷焦艾米利亚,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战士们将在红色旅中走到一起。
在这些人当中,有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奇尼[31](《无产阶级左派》的编辑),他来自雷焦一个拥有共产党传统的历史家族(他的祖母在1922年担任地区领导人,他的祖父是一名反法西斯战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他的父亲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后,便加入了游击行动小组[32])。他们中间还有法布里乔·佩里(Fabricio Pelli)(他后来死在监狱中)和普洛斯佩罗·加里纳里[33]。其他诸如阿佐利尼[34]、罗贝托·奥尼贝内[35]和弗兰科·波尼索利[36]等人,脱离官方左翼组织后加入了“公寓小组”(Gruppo dell’appartamento)。这个组织虽然也有正式名称(工人学生政治集团〔Collettivo Politico Operai e Studenti〕),但由于没有一个正式总部,很快就以“公寓小组”而闻名。
在1970年间,“公寓小组”与库西奥和《无产阶级左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建立红色旅时走到了一起(虽然不是组内所有人)。从党的传统中走出了游击队,这种事尤其发生在米兰和都灵的工人阶级社区,还有诺瓦雷斯(Novarese)的一些积极分子当中。
在其短暂生涯中(三个月发行了两版),《新抵抗运动》让自己成为了所有自主或地下团体的代言人,它们都认为必须用暴力回应资产阶级武装反革命。在这份出版物上,红色旅和其他小组联合发表了声明,当中就有游击行动队[37]。

费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
行动队与费尔特里内利
1970年末至1971年初,地下小组实施的一系列暴力活动通常都被当做是红色旅干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警察试图将一些更肮脏和挑衅性的事件归咎于红色旅,一般是“塑胶炸弹”袭击,爆炸现场也留下了红色旅的小册子。但红色旅否认用过炸弹,从下面的话就能看出这一点:“显然,炸药的使用不仅会吓到敌人,还会无差别波及无关群众,它也会让左派和右派做出最荒唐的解释,正因为这一点,反动派大量使用了炸弹。”
红色旅对“塑胶炸弹”袭击发表了大量的声明,称其明显是警方授意的法西斯活动。这份声明具体说明了其中的逻辑与目的:
我们袭击了暴君、老板的走狗,袭击了工人阶级
在工厂中最厌恶的人,这已经成为了必要,因为他们正在进犯我们的同志。
我们袭击了
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是今天资本反对工人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军队。
我们始终在袭击
人民的敌人,始终在斗争的广阔运动中发动袭击。
因此在一方面,我们相信没有同志会落入这些“自称”我们的法西斯分子用行动设下的陷阱,在另一方面,我们警告反动势力:
玩火终将烧到自己手指……
你们难逃惩罚!
警察和法西斯分子,你们听好了:对你们不会有半点怜悯,无产阶级正义的铁拳将痛打在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阴谋家身上。
阅读,传播,化为行动
红色旅统一突击队[38]
但是,这些自称红色旅的行动都被归咎于红色旅。在罗马便是如此,《新抵抗运动》将当时出现的一个小组称为“罗马的红色旅”。这个小组一直活动到1971年中,主要是对法西斯分子及其据点发动袭击(最出名的是对朱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39]的袭击,他是一场滑稽的未遂“政变”的参与者)。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也被尖锐地提出。虽然立场不同,红色旅还是接受了行动队的行动。

朱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
1970年4月16日,在“国家的屠杀”仅四个月后,游击行动队就大张旗鼓地出现了,当时全国一片混乱,法西斯分子在警方的“掩护”下越来越嚣张。晚上8点33分,一个声音闯入了正在播新闻的电视频道上。它在热那亚引起了剧烈反响。接着在其他地区(例如特伦托和米兰)也出现了“人民广播”。游击行动队的广播稿发表在了《工人力量》(它也发表了红色旅的声明)和《新抵抗运动》上。报上还详细说明了红色旅和行动队在政治意见上的分歧。
在那段时期出现的团体中,只有红色旅与行动队站稳了脚跟。他们懂得如何逃避警察的追查,并通过行动和“广播”引起政治讨论(政治小组“不断斗争”对武装团体的行动也越来越重要)。
除了广播外,行动队还对资产阶级权力中心(美国领事馆、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工厂、伊格尼斯仓库、加罗内精炼厂等等)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他们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做法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沿用了抵抗运动中的游击战模式:他们想仿效的不是“城市游击队”,而是古巴的山区(那里能够更好更久地防御)游击队。对于行动队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右翼政变。1970年12月7日的未遂“政变”给行动队的战士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当时,朱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亲王兼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第十轻型鱼雷艇分舰队[40]指挥官)带着一队法西斯密谋者,企图渗透并占领内政部。这本该是走向政变的道路。但出乎意料的是,密谋者们接到了取消行动的命令。一定是高层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后来对未遂政变的调查中,发现它又牵扯到一个叫做“风之玫瑰”[41]的右翼组织的另一个“密谋”,还涉及了军队的高层军官,导致维托·米切利[42]将军被捕,他曾主持过三年北约安全办公室和四年国防情报处(最重要的国家情报机关)。
对于这件事,红色旅和行动队的看法截然不同。红色旅认为,军事政变不是眼前的危险,瓦莱里奥·博尔盖塞不过是个小棋子。“更重要的是,政府和修正主义者想利用这些幻想。三年来,工人阶级不断在进攻。无路可走的政权必须在群众的眼皮底下,藏住它每天都在恶化的麻风病,于是编造了‘黑王子’(政变)的寓言,向公众舆论兜售。”[43]在红色旅看来,修正主义者(共产党和工会)想借此引诱阶级先锋队接受议会的把戏,遏制他们的战斗意志。
行动队的看法截然不同:“政变即将来临”。“工人力量”和“不断斗争”发表了文章强调:“国家军事力量和法西斯准军事力量的角色日益突出……只因消息泄露,才在最后一刻避免了一场……成百上千名军官、宪兵士官、意大利金融和产业资本,还有美帝国主义的代表……精心策划的政变……”[44]
自然,两个组织对修正主义分子的分析也不同。在行动队看来,“以意共为代表的传统左翼……日益担心地看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因此,它向共产党员号召:“工人阶级,工人们,大家都在要求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老板和帝国主义的广泛阵线与政策……党员同志们不加入革命的反法西斯阵线吗?”[45]
这段话听起来很像工人运动的历史话题:从第三国际的“人民阵线”策略,到武装保卫民主(比如游击队抵抗运动)。它与红色旅具有深刻的差异,这同样反映在了詹加科莫·费尔特里内利(后来发现他是行动队的创始人)的个性上。
自五十年代末以来,费尔特里内利一直是文化争论的主角。他的出版社和书店是意大利社会文化与政治复兴的一个重大典范。费尔特里内利书店于1950年成立,从此为工人运动的历史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化的重大空白。作为共产党员的费尔特里内利也逐渐把目光放在第三世界革命斗争上。
“费尔特里内利书店的小册子”相当及时地提供了正在发生的解放斗争和学生斗争的内容。费尔特里内利也越来越靠近革命左翼。他曾支持“镰刀与锤子”[46]脱党,最重要的是,他试图从共产党中找出从未放弃夺取政权、仍然想要抗争与革命的那些人。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在一些曾有游击队活动的环境下(尤其是利古里亚,据推断行动队就是在那成立的),诞生了最初的游击行动队。
在六八年代,费尔特里内利为了出版业务(他出版了切·格瓦拉和许多拉美重要小说家的作品)频繁访问拉丁美洲,同时为当时的游击队提供支持。他曾在玻利维亚被捕,为了争取他的释放,甚至还惊动了意大利总统。这位卡斯特罗和雷吉斯·德布雷[47](他曾在玻利维亚和切在一起)的朋友越来越确信意大利资产阶级无法掌控社会冲突,它将被迫诉诸专制(同样由于意大利在西方军事联盟中的地理位置)。
费尔特里内利认为,这是“政变和游击战”的阶段。他在一系列小册子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大利一九六八:游击队政治》(Italia 1968: guerriglia politica)、《政变的威胁仍在》(Persiste la minaccia di un colpo di stato)和《一九六九年夏季》(见上文)。他还出版了的埃德加·马赛尔·辛布(Edgard Marcel Simbu)关于刚果游击队的《雄狮之血》(Sangue dei leoni),后面附上了一本有用的城市游击战手册,它将成为运动的“秘传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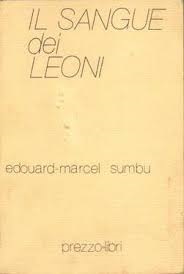

《雄狮之血》(Sangue dei leoni)1965年版和1969年版
对革命实践和问题的不断宣传与鼓动,让费尔特里内利成为了保守新闻界的眼中钉,后者没有放过任何机会来暗示他参与了各种行动。此外,警察和法官也频繁对他调查与审讯。自1970年初以来,费尔特里内利待在国外逐渐比待在意大利的时间还多。他从各地给意大利杂志寄来采访和文章,当中表明了自己的决定。他给《同志》(Compagni)杂志的一篇通讯中,表明了他的一些政治思考:
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走上战场进行战斗,才能阻挡反动派的进攻。如果说,过去我的政治活动总是以出版为媒介,那么从今天起,我承诺将不再置身事外。
[48]
1971年,费尔特里内利被怀疑参与谋杀汉堡的玻利维亚领事罗贝托·奎因塔尼亚(Roberto Quintanilla)。这位前玻利维亚秘密警察头目(他参与了谋杀切)被一名女子开枪暗杀,然后女子丢下了武器,是一把柯尔特蟒蛇.38,这把手枪是费尔特里内利的个人物品,他说他把这把手枪弄丢了。
1972年3月15日,一个农民在米兰郊外,塞格拉特(Segrate)一处高压塔下,发现了詹加科莫·费尔特里内利的尸体,死于爆炸。费尔特里内利之死及其带来的猜想,成为了那些年的一个主要话题。“民主派”和“运动派”的合作开始破裂,“内部敌人”的妄想症产生了。
最初,民主派认为费尔特里内利之死是“紧张战略”的结果,他死于“国家的谋杀”。当时众说纷纭,有许多猜测和矛盾的调查结果。民主派和议会外团体确信这是一场挑衅。“工人力量”第一个打破了谜团,它在一期报纸中揭示了费尔特里内利属于游击行动队,他的代号是“指挥官奥斯瓦多”(comandante Osvaldo)。
在议会外左派中,费尔特里内利的死重新激起了关于地下组织的讨论,“不断斗争”在论战中为“工人力量”辩护。“工人先锋队”和反国家恐怖主义全国斗争委员会指责“工人力量”和“不断斗争”:“它们对意大利的局势和运动的任务做出了错乱的分析,致使它们把行动队和红色旅当成了同志。”
除了争论之外,“民主派”与“运动派”的合作彻底破裂了。同样在议会外团体中,丰塔纳广场案后建立在激进民主的认同上,为了揭露“国家之谜”而建起的团结也瓦解了。
同志们的反应有两种:第一是寻求民主形式(参加选举、大选等等)。第二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是将自己孤立,退回到传统政党中。在这两种倾向下,他们都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虽然有些人还留在组织里,他们都淡出了,并且越来越关注地下武装团体,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武装斗争”必要性的广泛地下讨论,这场讨论将持续很长时间,导致议会外团体的基层组织四分五裂。
地下活动、思想与组织
在费尔特里内利死后,行动队的一些战士加入了红色旅,而在《新抵抗运动》停刊后,红色旅失去了半合法的代表,完全进入了地下。1971年9月,为了宣告他们的决定,他们散发了秘密小册子,包括这一本在内,多年后他们还将发表一系列的“理论反思”。
在这篇自问自答的文章中,他们强调民主制度已经露出獠牙。红色旅的政治思考似乎经历了突然而深刻的加速。老板和资产者处在千禧年的氛围中:历史在翻开新的一页,革命正有力地敲响大门。
这一思想上的加速是受到戴高乐在法国“搞政变”产生的印象与镇压气氛的影响。它的基本错误可能在于,认为“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整个无产阶级,而不仅是——即便是群众的——最进步的自主组织)感受的镇压气氛,与将反对压迫作为主要的、始终的、迫不容缓的目标的革命左翼感受到的程度是一样的。”[49]
纯粹意识形态上的阶级分析和对政权回应能力的低估,使得红色旅放弃了它——在诞生后的很长时间内还算是——正确的理论阐述。矛盾的是,它回到了费尔特里内利与行动队的立场,对意大利“转向反动”的必然性深感不安。
在这篇自问自答中,当问道:“你们认为法西斯是否会卷土重来?”红色旅回答:
问题不是玩弄词句……戴高乐在法国的“搞政变”和现在的“戴高乐法西斯主义”都打着民主的幌子。短期来看,这无疑是最不合适的模式。但是,如果指望经济和社会形势能够在革命斗争运动中保持稳定,那就太天真了……除了多年前,早被革命左翼批判的改良主义道路之外,我们还有两条路:参照无政府主义或第三国际的经验走工人运动的老路,或者将其与当代的城市革命经验相结合。
[50]
于是,红色旅在武装斗争中走得更远了,“它不是手无寸铁的群众运动的武装,而是统一的高潮。这不是要开启武装斗争,因为不幸的是,资产阶级已经单方面开始了武装斗争。”[51]
自然“没有理论,就没有革命”,红色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大城市游击运动的丰富经验”为参考[52]。于是,长期的“武装宣传”开始了。他们开展了一系列以儆效尤的行动,尤其是针对“工头”和法西斯分子,这是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
在1972年间,当时的政治气氛是那三年中最“火热”的时候,红色旅进行了意大利历史上的首次政治绑架:他们绑架了工程师伊达尔戈·玛奇亚里尼(Hidalgo Macchiarini),米兰西门子最遭人痛恨的管理层。这场行动是在强烈的社会对抗气氛中进行的。当年一月,工人们将马盖拉港封锁了整整两天。二月,“丰塔纳广场”案开庭,这场审判很快就变成了对“国家阴谋”的严厉指控。细致的反信息工作和以“释放瓦尔普雷达!恐怖主义是国家!”为口号的大规模运动,推倒了由法院和国家机器捏造的谎言之城。3月11日在米兰的一场人们记忆里最暴力的街头示威中,这座城市“停转”了好几个小时。人们还用“莫洛托夫鸡尾酒”对《晚邮报》报社发起了暴力袭击。
工程师玛奇亚里尼被用枪指着,绑到了一辆卡车上,经过二十分钟的“政治审判”后被释放。在“开庭”时,红色旅用了国家机器的语言:“审判”、“逮捕”和“缓刑”。当然,使用这种语言是为了讽刺,但它反映了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将在红色旅的武装活动中日益突出。它将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个集权的等级制组织、一个官僚的“政党机关”,再演变出“人民监狱”、“无产阶级审判”,甚至作为地下活动的必然结果,进行真正的“处决”。这一趋势预示着不经讨论就执行的铁的规则、好斗与服从。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将使红色旅越来越像国家的镜像,更难被运动所理解。
无论如何,这起最初的绑架在工人群众和一些议会外团体中,得到了普遍同情。“工人力量”在一份声明中做出了积极的分析:
在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历史上,一支工人队伍实现了第一起绑架。我们只需注意到,这一行动在工人阶级当中得到了肯定。这次行动中的新斗争方式也是值得肯定的。……在米兰工人阶级,也就是今天整个运动的先锋队看来,群众与先锋队的行动已经合二为一……
[53]
对拉伊纳特的行动(在试跑道纵火)持消极态度的“不断斗争”也在声明中表达了支持:“我们认为,这一行动符合群众的普遍意愿,即将斗争带入暴力与非法的领域。”[54]
在玛奇亚里尼被绑架的同时,法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雷诺公司的高管罗伯特·诺格雷特(Robert Nogrette)于1972年3月9日被新人民抵抗运动(Nouvelle Resistence Populaire)绑架,这是已解散的无产阶级左派(法)的武装组织。这起绑架在四十八小时后,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它受到了“不断斗争”的热烈拥护,后者还给它用了一个半页的大标题:“西门子和雷诺管理层的绑架案:革命的正义开始造成恐惧。革命正义万岁!”[55]
从1972年底至1973年初,围绕红色旅和“自发武装”问题进行过许多讨论。无疑,人们对红色旅产生了浪漫主义和普遍同情的情绪。打动积极分子,同样也打动基层工人的,是他们对工厂问题的干预、他们迅速有效的“工人调查”、他们有限度的暴力(直到1974年6月,红色旅没有在行动中打死过人,当他们在帕多瓦打死两名法西斯分子时,也会将其作为“工作事故”进行自我批评)以及他们讲起理论也通俗易懂。同样是1973年,红色旅在都灵工人组织中扎下了根。这一年里,法西斯的意大利全国工人工会联合会[56]的干部拉贝特(Labate)和菲亚特的人事主管埃托雷·阿梅里奥(Ettore Amerio)被绑架。这两起绑架案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是在议会外团体与菲亚特管理层的激烈争论中发生的,当时发现了大量的文件证明菲亚特指使警察和“法西斯代理人”对厂内先锋队进行“收买”、控制与镇压[57]。
工人们嘲弄般地散发了“审讯”阿梅里奥的“记录”,而法西斯工会干部拉贝特被绑在米拉费奥里门前的柱子上,晾在那里没人管,等警察来解救。
1973年菲亚特的重大占领与米拉费奥里派[58]的斗争,改写了革命左翼的全部格局。它一方面促使“有组织的自主运动”诞生,另一方面让红色旅不仅作为激进活动的标榜,更是成为了自主运动和革命团体的政治出路。这一过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
无产阶级武装核心与犯人斗争
1974年10月31日,佛罗伦萨的墙上到处都有一篇宣言,署名“无产阶级自主—圣十字自主集团与杰克逊集团”(Autonomia Proletaria-Collettivo Autonomo Santa Croce e Collettivo Jackson)。上面宣布了“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的无产者”卢卡·曼蒂尼(Luca Mantini)的葬礼,他与塞尔吉奥·罗密欧(Sergio Romeo)死在对佛罗伦萨储蓄银行的一次失败抢劫中。
卢卡·曼蒂尼是“不断斗争”的成员,而塞尔吉奥·罗密欧只是一名普通犯人。起初,这个消息引起了一些困惑,但从电话亭里传来另外两名被捕者(皮埃特罗·索菲亚〔Pietro Sofia〕和帕斯夸莱·阿巴坦杰洛〔Pasquale Abatangelo〕)的身份后,困惑就消失了:
10月29日上午在佛罗伦萨,五名战士落入了宪兵的埋伏……中弹的同志是无产阶级武装核心(Nuclei Armati Proletari)的战士。本次行动目的是筹备资金。他们的生命在弹片爆炸中消逝。两名同志死亡,另有两名受伤,其中一人重伤。另一人逃脱,目前处于安全状态。
[59]
“核心”并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组织,但这件事发生后,它不幸地出现在了新闻的聚灯光下。此前,“核心”都在那不勒斯、米兰和罗马活动。行动的目标都是监狱:米兰的维托雷(S. Vittore)、那不勒斯的波焦雷亚莱(Poggioreale)和罗马的雷比比亚(Rebibbia)。这些行动基本就是传播消息、鼓动普通囚犯和政治犯的斗争。监狱和所有相关机构(未成年监狱和收容所)都是它的主要目标。
“核心”是由被监禁的左派积极分子与犯法的广大普通囚犯在监狱中建立的。他们是“大地上的受苦者”运动(《大地上的受苦者》是弗朗兹·法农的一本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人民的知名著作[60])的继承者,并从1970年起得到了“不断斗争”的支持。他们也是六十年代以来最著名的囚犯,桑特·诺塔尼科拉[61](他是都灵的共产党员和作家,与一些人共同参与了数十起抢劫案,他的经历被记述在《不可能的逃亡》〔L’evasione impossibile〕[62]一书中)传奇的延续,后者当时仍在狱中。
在意大利地下武装组织中,“核心”属于最早的一批,很难给它的斗争策略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核心”最初的特点是,它诞生于南方的阶级社会中,也就是说,它诞生在一个以大量的非法边缘活动为特征(现在仍然如此)的生产与社会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在斗争和生活的选择上,在“有保障者”(通过关系得到稳定工作的工人)和“无保障者”(被从生产组织中驱逐出来,每天要出卖自己劳动力换取收入的工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这些阶层经常被称为“次无产阶级”、“边缘阶层”、“无保障者”和“法外无产者”,除了他们的生存条件不断将他们引向犯罪道路之外,他们还将监狱看做一条必经之路,看做对他们生活的一种调节。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在监狱的暴力与强制的关系下,最早一批普通囚犯的团体成立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已经成熟。该运动被称为“大地上的受苦者”,它受到了杰克逊兄弟(著名的《孤独兄弟》〔Soledad Brother〕一书)与弗朗兹·法农理论的强烈影响,并在“不断斗争”的活动范围内得到了合法性。
当时也是红色旅宣传“武装斗争”和建立“地下党”的必要性的年代。囚犯运动受到了复杂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于是决定不仅作为政治组织,也要成为真正的战斗组织。于是,为了自我代表,为了反抗这个造就了他们,又摧毁了他们的社会,无产阶级武装核心诞生了。因此,它的创建者都是监狱内外最坚定、最有决心的“法外分子”。在组织成立时,他们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要么反抗,要么死在监狱和贫民窟里”。这个戏剧性的生存选择,饱含着每个人经历牢狱之灾的痛苦与愤怒,而他们将在武装斗争中“脱胎换骨”。
“核心”接受了红色旅关于武装斗争和地下组织的理论,但他们舍弃了经典的第三国际工人组织模式。他们强调必须“摧毁监狱”,这正是因为,只有从监狱中才能诞生“法外”无产者的政治觉悟。他们短暂的斗争自然是在恐惧之下进行的。他们每个人的要求都经过了讨论。同时,他们在南方无产者中激起了极大的同情。这场转瞬即逝的悲剧,被批判国家恐怖主义的“民主进步人士”无视了。南方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被剥削者的宝库,是黑手党的后花园[63],它背后的残酷历史不断折磨着意大利人的公民意识。甚至在今天,我们的统治者在摧毁任何变革的苗头后,为了推行“紧急状态”的立法,还准备用“有组织犯罪”的借口再次将南方无产阶级作为实验品。
在经历了七十年代的剧变后,监狱仍未改革,却再次成为了社会冲突的主要调节者。法外无产者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向犯罪组织或监狱认命,要么在政治底层地位忍受屈辱。但是,他们只能有一个立场:要么革命到底,要么什么都不是。
在其短暂生涯中,“核心”遭受了严厉的迫害,包括冷血的谋杀、残忍的酷刑、严酷的监狱与身心上的摧残。在佛罗伦萨事件(当时宪兵没有警告,毫无必要地向曼蒂尼一行人开火)之后,维塔利亚诺·普林西佩(Vitaliano Principe)在那不勒斯被自己装的炸弹炸死,阿尔弗雷多·帕帕雷(Alfredo Papale)受伤,他的一只眼被炸瞎,身体也被爆炸撕裂,但他还是受了十四个小时的审讯。1975年,乔万尼·塔拉斯(Giovanni Taras)在袭击阿韦尔萨(Aversa)的啤酒节(matrimonio «lager»)时,死于爆炸中。同样在1975年,卢卡的姐姐安娜·玛利亚·曼蒂尼(Anna Maria Mantini)被警察杀害(警方称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1976年6月,有二十三名“核心”的战士被投入大牢,接下来的几年中还会有更多。在这些人中,阿尔贝托·布昂康托(Alberto Buonconto)将因恶劣的监狱条件发疯,在出狱后自杀。布昂康托的父亲对儿子的遭遇,讲了以下的话:
我是阿尔贝托的父亲。我不能,也不想在这里讲出个人感受。不仅是作为一名父亲,同样也作为一个人和公民,我只想谈谈那些冒犯了我感情的东西。
我只想表达,每一天想念阿尔贝托时的疑虑和苦恼。
阿尔贝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一个真诚和忠实的人。
直到今天我还在想,为什么他受到了如此残忍、如此无情的对待,为什么在他被捕后,要在漫长的监禁期间对他动刑,正是这日复一日的折磨导致了阿尔贝托的毁灭。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也许能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希望在我的儿子阿尔贝托身上发生的事不会在明天继续重演。不幸我们都很清楚,它今天还发生在其他孩子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想加入这本书的写作,它汇编了关于阿尔贝托悲惨经历的证言。
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天,其他法官能够审判或者谴责那些杀害我儿子的人。
在阿尔贝托被抓走的前一天下午,宪兵和几个特别处的人
[64]来家里搜查。他们来了七个人,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后援引了第80条(未经许可的调查),进到我们家翻找东西,顺走了一些阿尔贝托和他几个朋友的照片。我的妻子抗议说,法律没说过能让他们带走照片,我们只能用武力把照片拿回来,但代价会是什么呢?
在经过了非常仔细的,但其实根本没用的搜查后,他们要求我和女儿宝拉跟他们上警局。我的妻子就待在家里。
疲惫的宝拉要求乘电梯,他们却挑衅说,狱里可没有电梯,这差不多是在暗示她也有罪。
他们让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待了几个小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官员来问,我对儿子都了解些什么。为什么不给他家里打电话?他离开那不勒斯多久了?为了弄明白我有多了解我的儿子,他们假惺惺地问我这些。这些问题都是陷阱,因为阿尔贝托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正在殴打他、虐待他。我当时还没发觉这些。
后来,我从律师和报纸那里得知,阿尔贝托受伤了。他们说不知道是谁做的。不知道是谁!他是在公家的办公室里受伤的,如果他们想的话,很容易就能查到是谁干的。
从那天起,我们都陷入了绝望。我的儿子在反对不平等与不公正的斗争中,献出了他的生命。总有一天,我的儿子,我的阿尔贝托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将向那些造成压迫、欺凌和杀戮,手握权力的冷血的家伙算账。
要算的账还有很多。
[65]
释放所有人
(皮诺·马西)
有很多同志
从我们身边被夺走
因为这正义
要他们入狱
但他们并肩着
要在监狱里
度过一生的
其他无产者
他们正组织起来
为了让囚犯们
成为反对老板
的斗争基础
为此他们还
需要我们的保护
如果我们在外战斗
对他们将是帮助
释放所有人
就是继续战斗
就是继续组织
不浪费一个小时
猪头老板
这让你们激动
你们没有监狱
来把我们关起来
我们会让你们
让我们的剥削者看看
里面每有一个
外面每有千个在战斗
我们都是罪犯
但只是对于老板
我们都是同志
革命的同志
所有的改良主义者
充当告密者的人
和老板站在一起
我们就消灭他们
释放所有人……
→ 《释放所有的人》视频版
|
七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问题
六九年底,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是组织和战略问题,以及对新社会形式的想象,还有围绕“拒绝工作”和阶级构成的概念。
第一个问题是厂内组织的形式。从新的自我组织运动的诞生起,工人普遍产生了觉悟,他们把批判的矛头转向工会。对工会的批判有不同的层面:首先是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层面:工会具有系统性的调解作用(包括与雇主协商协议)。
第二个层面更为重要和复杂:它激进批判了工会作为调解机构,同时不言而喻,作为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机构和制订劳动力售卖价格的工具的职能。
第三个层面将工会看做是被引入工人斗争中的一种进行控制、诱发分裂的政治手段。出于这三点,革命组织对工会表现出敌意。于是,新的组织形式在工会之外诞生,它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工会,并在与后者的对抗中发展了激进和破坏性的批判精神。
另一方面,工人主义杂志,尤其是《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抱着这一态度进行了理论研究。《工人阶级》的立场很明确:自从工人斗争被分为经济斗争(由工会管理)和政治斗争(由党管理),雇主和资本主义国家就瓦解了工人斗争的变革潜力,让战后工厂的革命工人陷入无力和分裂。
为此,要让协议的胜利成为政治上的重大胜利,这意味着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同样,还要让秋天的斗争运动去反对协议本身,反对这个给劳动力订价的制度。劳动力的价格以及使用(工资和工作条件)不应是每两三年由上层、由雇主组织和工会商定的东西,而应当成为不断动员、不断讨论的对象。从协议开始,必须彻底瓦解工厂制度、资本主义分工与雇主的统治。最终,从协议冲突开始,必须在工厂中建立工人权力。
工厂委员会就是夺回这些阵地,将对工会的批判转向能够表达基层意志的、统一组织形式的尝试。六九年秋天让委员会的经验传遍了各个工厂。从一开始,委员会就得到了响应,也遭到了反对。当然,它受到官僚工会的反对,因为一个由选举产生、广泛代表工人的机构,将会剥夺它在工人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易与协商的作用。
此外,尤其是在最落后的地方,委员会受到了雇主的百般迫害,因为雇主看到了这些组织能够协调革命力量,而这些力量直到那时还没能组织起来,仍在盲目地消耗着。
然后,委员会还受到左翼的反对,尤其是靠近“不断斗争”和“工人力量”立场的工人和积极分子,还有自主集会与基层委员会的反对。这些人尤其批判委员会的两点:首先,它重新引入了代表制度,削弱了自我组织的压力,还有基层、部门与车间的压力(“不断斗争”以“我们都是代表”的口号来回应工人代表的选举)。其次,他们批判委员会和工会一样起阶级调解作用。
自六八年代以来,在分开斗争的原则下,自主斗争和工会谈判是严格分离的。这项原则为工人行动、新的组织与生产模式的设想,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这项原则使工人组织的命运不必与雇主的协议相连,在大多数工人对协议不满意时,也能够保持行动的自由。现在委员会又将战斗和谈判重新连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恢复了工会对工人组织进行控制的条件。
关于委员会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没有得出定论。大部分革命群众认为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自我组织,于是便参与其中。一部分革命群众保持批判的立场参加了它。更激进的革命群众反对它,继续建设基层组织,正面反对工会。为了理解对委员会的批判,我们引用了发表于1973年的米兰阿尔法·罗密欧、倍耐力与西门子的自主组织的文件:
工会组织正所处的阶段要求它公开与改良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重建计划合作。目前老板势力的猛攻是为了将仍在反抗的左派釜底抽薪,迫使工人阶级屈服于资本计划。
说工厂委员会是基层的组织工具,它是工人阶级更加自主的结果,这是不准确的。相反,显然面对基层的推动、面对工人自主的发展,工人往往脱离了工会高层的控制,后者被迫向更基层的组织模式让步,但同时又得到了进行控制的更大可能性。如果我们回顾工厂委员会成立至今的情况,那么只能看到,它们始终受到工会的完全控制。它遵循工会的路线时,就被允许活动,反之,要是基层的要求占了上风,它就要被阻止。
在实践中,工厂委员会的确表现出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按照战斗性工人的想法,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战斗的政治组织,还代表着实现社会构想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它成为了工会在工厂内部的分支,不让工人要求工人组织表现出革命性的强大冲动。
但在这里,不仅需要分析表面,还要深入本质。革命团体和基层自主组织提出了什么分析和理论?我们已经阐述了工人斗争浪潮——从六八年春天开始,在六九年秋天达到高潮——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包括工资平等、降低工作速度和工作量、要求最低工资、反对有害工作环境以及要求降低物价。
但是,这些目标本身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战略框架,或者一个完整而有机的革命计划。因此,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一个在那些年,甚至在整个七十年代都处于中心地位的概念上,虽然围绕着这个概念产生了许多谬误、曲解、歪曲与不恰当的表达,它就是拒绝工作。
拒绝工作(节选)
……为了理解“拒绝工作”,让我们来分析它的两层含义。首先,拒绝工作是无产阶级在先进工业生产周期中的直接行为,他们还未屈服于现代化工业,几乎是凭借本能在反抗。
受过教育的皮埃蒙特人认为在菲亚特工作是一种世袭的命运,他在奋斗价值观的熏陶下成长,也许能承受住汽车制造业繁荣那几年愈演愈烈的剥削。但在海滩和阳光下长大的卡拉布里亚人看来,这种狗屎般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卡拉布里亚人的认知是健康的,他能看出其中的不合理。从这个角度来讲,拒绝工作是一种直接的反应,但也是具有远见的:这种奴隶制不仅是工人无法忍受的,它对社会也无用。
在这里,我们来看拒绝工作的另一种含义, 从“拒绝工作”来解读社会运动与历史转向。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整个历史,都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拒绝在物质再生产中,付出注意力、劳力、技术力与创造力的历史。这一拒绝产生了阶级的划分(一部分人拒绝工作,让另一部分人替他们工作、受他们奴役)。但是,在社会的集体智慧控制与指导下,“拒绝工作”能够利用技术和机器将人从雇佣劳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66]……
占领米拉费奥里与作为政治出路的自主运动
1973年标志着意大利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与革命左翼组织形式的重大转折。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工人占领了菲亚特的米拉费奥里工厂,这场协议冲突的戏剧性结局是自六八年代以来的整个自主斗争周期的高潮。
前几年(1971—72年)经历了议会外左翼团体的危机和工厂斗争的退潮。与此同时,活跃的社会团体开始在大城市出现。运动的重心正在从工厂转向社会。在这一转变中,占领菲亚特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此外,米拉费奥里的占领宣告了革命团体的无力,它们已经失去了先锋队的作用。
在三月期间,都灵酝酿了给抵制协议的雇主最后一击的条件。工会方面要求建立一个统一标准,在待遇上实现平等,包括提供假期、实行五天四十小时(周六也休息)工作制、减少强制加班。工会在三月草拟了一份不令人满意的协议,受到了工人的强烈反对。菲亚特的工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自发斗争,在当月中旬坚定地发动了罢工,这场罢工很快蔓延到米拉费奥里的全部车间,其他工厂也都加入了进来。
各车间内部每天都搞游行,即便如此,27日还是传出了因为罢工时间过长(超过一百七十小时),管理层不打算接受协议的消息。29日上午,革命团体——尤其是“不断斗争”和“工人力量”——带着小册子来到厂门口,再次坚定地发动罢工。但工人那天早上来上班时,天气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然后,就在上工后不久,传来了决定占领工厂的消息。后来,在《新闻报》(La Stampa)宣布达成协议的同时,工人们走出去,在厂门口插上了红旗。
占领的组织过程对于所有人,甚至对于工人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谜。但很显然,厂内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拥有新社会背景的工人已经让工厂的行为方式脱离了共产党的运动传统。这些行为方式来自于新一代无产者的日常生活。他们不是从农村被连根拔起、刚来到大城市的南方农民工,而是年轻的都灵人和上过学的皮埃蒙特人,他们在学生斗争的氛围和街道集会的经验中成长起来。占领米拉费奥里是第一次青年无产者争取解放的示威,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仍在坚持斗争,直到七七年的爆发。
占领米拉费奥里时,工人表现出了激进的立场,自发拒绝了劳动义务。拒绝工作已经成为了一场自觉的运动,但还没有在工厂内建立自己的组织关系。在被占领的日子里,米拉费奥里是一座攻不下的城堡,国家不敢轻易下场。但这并不关键。老板屈服了,工人在基本的平等问题上(假期、规定和减少加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问题不仅如此。运动必须有另一个方向和新的视野。随着石油价格上涨,危机的征兆露出水面,紧接着是通货膨胀、失业、整个产业的衰落、黑色产业链的扩大,这些都是城市化的恶果。第一批大城市的原住民、系着红领巾的年轻工人,发出了无意义的口号、不带威胁和誓言的呼喊,这些声音宣告了意大利革命运动新一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没有什么进步思想、没有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没有对民主制度的任何感情,也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神话的尊重,它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在这样的转变中,工人自主的新政治文化现象得以形成。
“工人自主”是工会和革命团体泛用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工会自主。在六十年代,工会独立于政党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它还带有模糊的改良主义与工人斗争去政治化的含义。而工人自主应当意味着脱离工会与左翼政治控制的斗争的自我组织。
但在1973年,“工人自主”一词有了新的意味,一种更激进的含义。它开始表示工人阶级自己,即团结的无产阶级能够集体组织交换与生产的社会条件,以及在资产阶级合法性下实现自主。人们还要由自己来交换、分配时间与财产。自主的原则完全实现了: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的领地确立了自己的规则与实践。这场运动迅速蔓延开来,让议会外团体陷入危机。
在革命团体中,有一些小组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意义。葛兰西小组[67]曾批判过列宁主义领导模式和小组的组织形式,并寻求通往社会解放的基层组织形式。“工人力量”验证了米拉费奥里的教训,三月的几个月后,它决定将组织解散。同样,“不断斗争”也从内部开始瓦解,并在1976年10月急剧分裂。
11月宣布解散的“工人力量”在报纸上讨论了米拉费奥里的教训:“3月29—30日在米拉费奥里,里瓦尔塔(Rivalta),在整座菲亚特发生的坚定罢工变成了一场武装占领。面对老板和工会从1969年9月至今的所有压迫,工人们以这种方式,直接由自己接管了权力。米拉费奥里派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镇压和技术重建的手段都是徒劳的……”
历史性妥协
“历史性妥协”的说法出自1973年,当时的共产党高层对智利法西斯政变进行了反思。但不要认为这一说法是什么新鲜东西,它不能算作意共的政治转向。
相反,“历史性妥协”仅代表意共自1946年以来的战略改变了政治术语。随着时代的不同,这一战略又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新多数派政治”,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不断在改良主义实践与革命辞藻之间寻求平衡。
陶里亚蒂去世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主要是学生)因两大事件脱党。第一个事件无疑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既让旧的斯大林主义干部反对赫鲁晓夫,也对新的学生党员产生了强烈影响,让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比如:“少数人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真理往往站在了他们一边。”
第二个事件是工人斗争的回归,它表明了战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与党的传统文化没有太大联系的人们往往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陆续来到北方工厂的南方农民工。
六八年代后的意共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潮流之间。一方面,它通过选票和社会影响力,得以利用学生运动的动力。另一方面,它在新的革命群众中丧失了权威与主导权。六九年,头一会出现了独立于工会和党领导的、群众性的工人自主斗争。
在六十年代中期,工人阶级和党的关系问题多次被重新提出,尤其是在六六年的热那亚代表大会,党在这场会议上决定重建自己在工厂中的地位。这正是共产党的根本问题。由于党在政治行动中以国家经济整体利益为准绳,任何反生产主义、平等主义和激进反资本主义的动力在党内都无法找到适当的表达。
面对新的工人阶级形成,还有随之而来的农民工和年轻工人的登场——他们与共产党政治传统,与歪曲了葛兰西主义的“生产主义”神话,尤其与主流工人运动的国家主义文化格格不入——共产党越来越快地失去了对工人斗争的掌控。
对于工人的激进态度,意共采取了与中产阶级结盟的政策。直到六十年代,它的政策都是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与政治主导权,在六八年代以后,甚至在“火热之秋”后,它的政策似乎只是出于一种共识:打击工人的政治力量。
1973年无疑是革命群众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关键一年。这是出于两个对立的原因。在米拉费奥里的占领之后,工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信号:无需党和工会,他们就能自主占领意大利最大的工厂。而党和工会是明确反对这些做法的。
意共则从智利政变中收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信号:即使成为了多数派,也没法与资产阶级正面对抗,因为这会引起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因此,需要与资产阶级最大的政党妥协,因为后者代表了全国的所有社会力量。整个社会的紧张局势加剧。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演变为了彼此的分裂与暴力对抗
但在1973年后,党和先锋队之间的分歧呈现出了其他形式,它们比单纯的政治纲领上的分歧更加深刻和戏剧性。城市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两大部分开始分裂,有保障的无产者与无保障的无产者之间产生了划分,这是七七年代导致左派危机的最重要原因。
当我们说无保障的无产者的时候,指的不仅是失业者、学生、正在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也包括新的劳动力中,受到重组和裁员影响最大的那些人,这是七十年代起的生产力发展与技术改造的必然结果。
例如,危机在饱受争议的因诺琴蒂事件中浮现,当时雇主解雇了三分之一的员工,他们都是年轻工人,许多人和自主政治组织有关系。1976年秋天,被解雇的工人(他们想和几百名自主积极分子和学生一起回到工厂)和意共的老工人(到那时为止,雇主都没有动他们的工作岗位)之间发生了冲突。
面对无保障者运动(它在七七年代迸发出全部的规模与破坏力)的出现,共产党与它针锋相对,还采用了挑衅的方式,间接煽动革命团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走向武装斗争。
1976年选举的胜利,加上有大量奴性十足、专门应声附和官僚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共产党甚至提出了最疯狂的自杀口号:工人阶级成为国家。当危机正摧毁着工作岗位,国家准备向不安分的失业工人发起进攻的时候,做出这一声明、提出这一口号,无异于在运动内部、在左派和无产者中间播下分歧的种子。后来七七年代发生的一切,也是这一政策造成的结果。但是为“历史性妥协”和“工人国家化”战略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意共自己。
共产党带着偏见拒绝了任何无保障的自主运动无产者的建议,不加批判地将自身与意大利资产阶级——其试图通过重组来摆脱危机——的需要相结合,拒绝了工人斗争本身的要求,拒绝了往失业者与青年要求的方向——缩短普遍工时——进行斗争与变革。
在七七年代,当最初的工人自主集会发起时,在运动的要求下,在全国工人大会上(四月在里利科举行)以及工会的广大部门中提出了口号:“少干工作,一起工作”,“减少工时,同工同酬”,共产党把它当做是对自己的挑衅,于是拒绝了它们。
它最终为自己的闭塞和对雇主的奴性付出了代价,仅仅三年之后,阿涅利——由于共产党帮他把工厂里的“桶底”(这是反工人的共产党员阿达尔贝托·米努奇[68]的说法)都赶了出去,他才能抬起头来——就赶走了四万名工人,摧毁了工人组织和共产党自己的全部势力。从那一刻起,意大利共产党走上了绝路[69]。
[1] Brigatte Rosse, cit.——原注
[2] 同上——原注
[3] 补助资金管理局(Cassa integrazione)意大利中央福利机构,几乎无期限地保证了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失业救济金。在整个七十年代,为了推动自我组织与涉及拒绝工作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许多个人和集体的试验有意识地将这些收入形式作为工具来使用。显然,从七七年的失败后,管理局变得更为慷慨,它被明确而有效地用作了控制与瓦解动员的工具。——西译者注
[4] 同上——原注
[5] 同上——原注
[6] 同上——原注
[7] 同上——原注
[8] 同上——原注
[9] 雷纳托·库尔乔(Renato Curcio,1941年9月23日—— ),意大利散文家、社会学家。1961年起参加左翼运动。1969年参加了“火热之秋”。1970年创立红色旅,并策划了多次行动。1972—1974年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74年被捕。1975年越狱逃走。1976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28年徒刑。1993年获假释。1998年获释。——中译者注
[10] 同上——原注
[11] 弗兰科·皮佩尔诺(Franco Piperno,1943年1月5日—— ),意大利记者、散文家、物理学家。早年参加了意共。1968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出党。1969年参加了“火热之秋”,同年参加了“大众工人”运动。1978年莫罗被绑架期间,试图撮合双方谈判,但未果,被迫流亡法国和加拿大。回国后被判处2年徒刑,此后脱离武装斗争活动。2006年曾被提名竞选总统。——中译者注
[12] 不要将它与缩写词相同的1975年米兰国立大学的学生组织相混淆。——原注
[13] 见《红色旅》。——原注
[14] 《六九之夏,意大利政变、彻底且专制的右转之迫在眉睫威胁》,ESTATE 1969. La minaccia incombente di una svolta radicale e autoritaritaria a destra, di un colpo di stato all’italiana。——原注
[15] 瓦西里斯·瓦西里科斯(Βασίλης Βασιλικός,1934年11月18日—— )希腊作家、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担任记者。1967年政变后,相继流亡意大利、法国和美国。1981—1984年任希腊国家电视频道(ET1)主任。1981—1984年任印第安纳国家石油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回国。1996—2004年任希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2019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16] 《希腊也不可能》,Anche noi non credevamo che in Grecia fosse possibile。——原注
[17] 图帕马罗(Tupamaros),全名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Tupamaros,MLN-T),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乌拉圭的一支左翼游击队。早年从事政治绑架活动,70年代初开展游击活动。1972年被乌拉圭军队击溃后瓦解,主要领导人基本被捕。1984年获大赦。——中译者注
[18] 同上——原注
[19] 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是联邦德国的一个极左翼准军事组织,1970年成立。红军派成立后即针对联邦德国军警人员从事暗杀和袭击活动,并曾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训练。1972年其主要领导人悉数被捕,被捕后在狱中绝食抗议,多数领导人在1976年遇害,红军派暂时转入地下。1977年红军派再次开展大规模袭击活动,并于1977年9—10月制造了“德国之秋”,期间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合作进行绑架活动。1984年在各方打击中大部被捕,少数成员逃往民主德国。1985年起恢复行动,但力量大不如前。1993年制造了最后一次袭击。1998年宣告解散。——中译者注
[20] 同上——原注
[21] 皮诺·马西(Pino Masi,1946年1月26日),意大利吟游诗人。早年即参与工人运动。1966年起在歌剧院演出。1970年起参加新左派运动。1972年为帕索里尼的电影《十二月十二日》配乐。1975年起对新左派运动悲观失望,脱离活动,专心创作。——中译者注
[22] 皮耶罗·尼西姆(Piero Nissim,1946年2月5日—— ),意大利音乐家。——中译者注
[23] 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Spiro Theodore Agnew,1918年11月9日——1996年9月17日),美国政治家。1941年入伍,二战期间随英军在巴伐利亚作战。1947年加入共和党。1951—1952年期间参加朝鲜战争。1967—1969年任马里兰州州长。1969—1973年任副总统。1973年,因在马里兰州州长任上私自收受工程承包款回扣一事曝光,被迫辞职,随即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24] 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1916年6月9日——2009年7月6日),194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1961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1968—1981年任世界银行行长。2009年逝世。——中译者注
[25]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70年12月14日在格但斯克血腥镇压罢工,12月20日被解除一切职务,被迫退休。——中译者注
[26] 同上——原注
[27] 这里的粗体是我们加的——原注
[28] 同上——原注
[29] 同上——原注
[30] 无产阶级左派(La Gauche prolétarienne〔GP〕)是法国的一个极左翼政治团体,1969年成立。组织成员大部分来自于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马列)(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éninistes),支持毛泽东主义,既反对法共,也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无产阶级左派成立后即被禁止合法活动,多次发起地下斗争。1973年11月宣布解散,部分成员继续在《解放报》工作,部分成员另行组建国际旅(Brigades internationales),残余成员参加了毛主义共产党。为了将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与《无产阶级左派》(Sinistra Proletaria)相区分,在这里分别将它们简写为无产阶级左派(法)和无产阶级左派。——中译者注
[31] 阿尔贝托·弗郎切斯奇尼(Alberto Franceschini,1947年10月26日—— ),出身于共产党人家庭。早年参加了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1969年退党。1970年加入红色旅。1974年4月18日参与了绑架检察官马里奥·索西(Mario Sossi)的行动,同年9月被捕并被判处60年徒刑。1982年脱离红色旅。1987年获假释。1992年获释。——中译者注
[32] 游击行动小组(Squadre di azione patriottica,SAP)是二战期间意大利的一支游击队,1944年成立,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并与加里波第旅保持密切联系。1945年5月,同加里波第旅一齐解散。——中译者注
[33] 普洛斯佩罗·加利纳里(Prospero Gallinari,1951年1月1日——2013年1月14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参加了意共。1969年退党,参加了“公寓小组”。1970年加入红色旅。1974年因参加托斯卡纳银行抢劫案被捕。1977年越狱逃走,同年11月2日实施了对基督教民主党人普布利奥·费奥里(Publio Fiori)的未遂刺杀。1978年3月16日策划并实施了绑架莫罗的行动,5月9日支持处决莫罗。同年12月21日参加了对基督教民主党人乔万尼·加洛尼(Giovanni Galloni)的未遂刺杀。1979年5月3日领导了对基督教民主党总部的袭击行动,同年9月24日在与警方交战中重伤被俘。1983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坚持斗争。1996年获假释。2013年逝世。——中译者注
[34] 劳罗·阿佐利尼(Lauro Azzolini,1943年9月10日—— ),早年参加了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60年代末加入意共。1974年加入红色旅,曾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红色旅的后勤工作。1978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后获假释。——中译者注
[35] 罗贝托·奥尼贝内(Roberto Ognibene,1954年8月12日—— ),1968年加入意共。1969年退党,并发起成立了“公寓小组”。1970年加入红色旅。1974年6月17日参与袭击了“意大利社会运动”总部,10月15日在与意军交战中重伤被俘。1975年被判处28年徒刑。1979年在阿西纳拉监狱(Carcere dell'Asinara)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改判13年徒刑。1983年脱离红色旅。1990年改判18年徒刑。1993年获假释。——中译者注
[36] 弗兰科·波尼索利(Franco Bonisoli,1955年1月6日—— ),1977年加入红色旅。1978年3月16日参加了绑架莫罗的行动,10月1日被捕。1983年被判处4年徒刑,此后脱离红色旅,并获假释。——中译者注
[37] 游击行动队(Gruppi di Azione Partigiana,GAP),又名游击行动队—人民解放军(Gruppi d'Azione Partigiana - Esercito Popolare di Liberazione),是加尔尼亚诺侯爵,贾詹科莫·费尔特里内利(Il marches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di Gargnano)于1970年创立的一支游击队,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格瓦拉主义,试图寻求苏联支援,推翻资产阶级政府。1970年春开始活动。1972年费尔特里内利遇害后解散,其余成员大部分参加了红色旅。——中译者注
[38] 同上——原注
[39] 朱尼奥·瓦雷里奥·博尔盖塞(Junio Valerio Borghese,1906年6月6日——1974年8月26日),意大利将军。1922年入伍。1937—1939年期间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期间曾指挥袭击了直布罗陀。1943年墨索里尼另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萨洛共和国)后,出任第10军军长,残酷屠杀游击队员。1945年向美军投降。194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旋即改判为12年徒刑,并在陶里亚蒂的指令下获释。1951年加入“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并于1951—1953年担任名誉主席。1968年成立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Fronte Nazionale)。1970年在美国默许下发动政变,企图恢复法西斯主义统治,政变失败后流亡西班牙。1974年在加的斯暴卒。——中译者注
[40] 第十轻型鱼雷艇分舰队(Decima MAS/Motoscafi Armati Siluranti)是二十世纪初组建的意大利海军的一个单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由博尔盖塞领导,它并被指控对游击队开展了大量行动,谋杀了许多人。因此,博尔盖塞被判入狱一段时间,不久后被释放。后来他成为了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主席。1970年,他显然与未遂政变有关。政变失败迫使他出逃到西班牙,于1974年在那里去世。——西译者注
[41] “风之玫瑰”(Rosa de los Vientos)是意大利的一个新法西斯主义秘密组织,成立时间不晚于1961年。曾被怀疑策划1961年南蒂罗尔“大火之夜”(Notte dei fuochi)。1973年起与北约情报部门和意军建立联系,企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1973年10月阴谋泄露后,组织成员相继被捕。1974年瓦解。——中译者注
[42] 维托·米切利(Vito Miceli,1916年1月6日——1990年12月1日),意大利将军。1934年入伍,参加了埃塞俄比亚战争。二战期间在东非作战,被英军俘虏并被囚禁于印度。二战后回国,后进入北约工作。1969—1970年、1970—1974年任意军国防信息服务部主任。1972年接受美国资助,企图同新法西斯主义团体“风之玫瑰”(Rosa de los Vientos)合作推翻政府。1974年被捕。1978年获释。1976—1987年任国会议员。1980—1982年任特拉帕尼市议会议员。1990年在法国治病时暴卒。——中译者注
[43] 同上——原注
[44] 同上——原注
[45] 同上——原注
[46] 镰刀与锤子(Falce Martello)是一个在塞斯托-圣乔万尼(Sesto S. Giovanni)地区有1500名成员的意共组织,它在后来建立了意大利共产主义同盟(马列)(Unione dei Comunisti Italiani marxisti-leninisti),后成为“为人民服务”(Servire al Popolo)。——原注
[47] 茹勒·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égis Debray,1940年9月2日—— ),法国作家、哲学家。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1965年跟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被俘,在遭受残酷虐待以后被判处30年监禁。1973年在萨特、阿连德、聂鲁达等人的斡旋下获释回国。1979年赴尼加拉瓜,参加了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起义。1981年、1988年两次支持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1982—1992年任太平洋共同体秘书长。2002—2004年任欧洲宗教研究所所长。2009年支持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2010年支持左翼阵线。——中译者注
[48] VV. AA. L’affare Feltrinelli, Milán, Stampa Club, 1972.——原注
[49] Brigate Rosse, cit.——原注
[50] 同上——原注
[51] 同上——原注
[52] 同上——原注
[53] 同上——原注
[54] 同上——原注
[55] 同上——原注
[56] 意大利全国工人工会联合会(Confederazione Italiana Sindacati Nazionali dei Lavoratori,CISNAL)成立于1950年,它是“意大利社会运动”(MSI)的工会。1966年,它改名为工人总同盟(Unione Generale del Lavoro,UGL)。——西译者注
[57] 1971年,菲亚特被发现曾在五十年代收集了上千份工人档案,用以解雇、敲诈和威胁工人。这些情报的收集得到了警察、宪兵和特务机关的帮助。——中译者注
[58] “米拉菲奥里派”(partido de la Mirafiori),指政治团体陷入危机后,推动厂内自主集会的、菲亚特工人在斗争中形成的复杂工人政治结构。--中译者注
[59] Alejandro Silj, op. cit.——原注
[60] Ed. cast.: Los condenados de la tierra, México, FCE, 1963 (y sucesivas reimpresiones)——西译者注
[61] 桑特·诺塔尼科拉(Sante Notarnicola,1938年12月15日——2021年3月22日),意大利诗人。早年参加了意共,后退党,转向无政府主义。1963年起参与了18次抢劫。1967年在袭击那不勒斯银行失败后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后在狱中积极参与“火热之秋”。1976年企图越狱未遂。1995年获假释。2000年获释。2021年因新冠肺炎引发的并发症在博洛尼亚逝世。——中译者注
[62] Sante Notarnicola, La evasione impossibile, Milán, Feltrinelli.——原注
[63] 战后的南方黑手党和资产阶级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手党帮助基督教民主党的竞选和政治活动,作为交换,黑手党得到当地的合同、得到从事非法活动的许可、能够参与走私、垄断农业用水和土地投机。例如,历届政府指定给西西里的大笔基金和地方征税都被用于黑手党的毒品生意。——中译者注
[64] 一般调查与特别行动处(Divisione Investigazioni Generali e Operazioni Speciali,DIGOS),意大利警察机关,负责恐怖和政治活动的情报与镇压。——西译者注
[65] Franca Rame, Non parlarmi degli archi, parlami delle tue galere.——原注
[66] 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拒绝工作”一是对剥削的拒绝,二是对异化劳动的拒绝。“拒绝工作”在战后成为了普遍现象,这对于今天的国内读者来说也不难理解,因为它是雇佣劳动固有的特点。——中译者注
[67] 葛兰西小组(El Gruppo Gramsci),成立于米兰,成员有来自北方地区和瓦雷泽的工人、教授和知识分子。——原注
[68] 阿达尔贝托·米努奇(Adalberto Minucci,1932年3月4日——2012年9月21日),意大利记者。1950年加入意共。1955年当选为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厂工会代表。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担任意共都灵地区领导。70年代曾任《复兴》(Rinascita)杂志编辑,并担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1992年任国会议员。1991年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仍留在党内。1992—1994年任参议员。1993—1997年任奥尔贝泰洛(Orbetello)市长。1998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人党(Partito dei Comunisti Italiani),并为党刊《左翼复兴》(La Rinascita della sinistra)撰稿。2012年在罗马逝世。——中译者注
[69] 1978年3月16日,红色旅在罗马市中心绑架了阿尔多·莫罗,击毙了他的5名保镖,将他扣押了55天后处决。莫罗是意共进入政府铺平道路的关键人物,红色旅的目标是意共及其“历史性妥协”的政策。目的是阻止意共加入政府后,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化。结果却加剧了这一过程,因为革命危机已经过去,即使阻止意共反映了运动的愿望,工人阶级也无力削弱国家。详见下文。——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