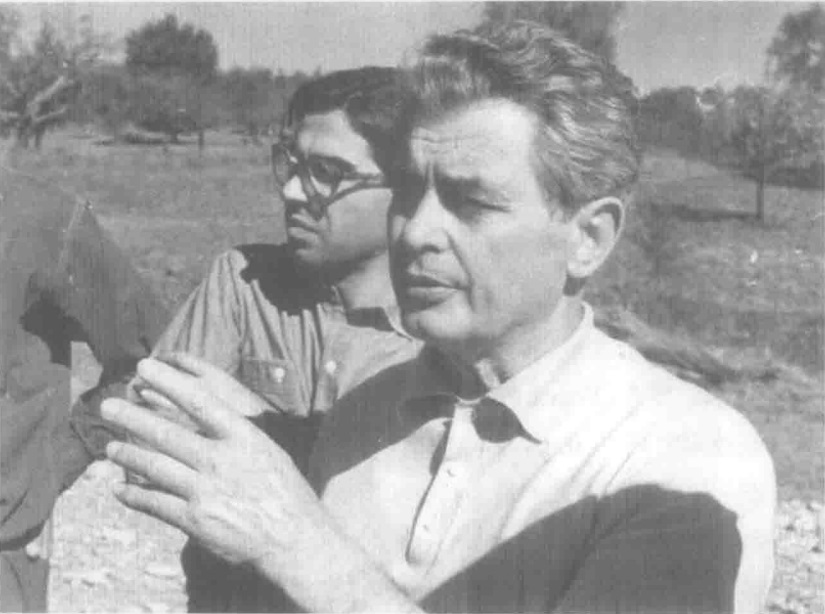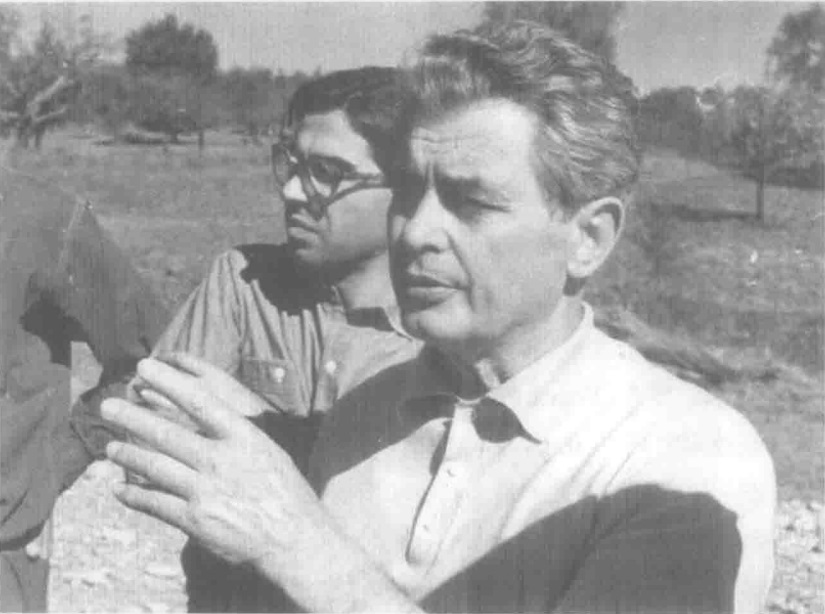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1999)
伊文思与意大利纪录电影
〔意〕维尔吉利奥·托西
孙红云 译 胥弋 校
20世纪50年代,电影是最受公众喜爱的娱乐形式。在意大利,电影院的平均上座率非常之高:据统计,平均每人每年看十二场电影,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成年人每月去电影院两到三次。
意大利的故事片在电影史上非常重要,作为新现实主义的艺术遗产,它至今仍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纪录片的状况却一直不乐观,至少就影片的质量而言,是非常糟糕的。拥有百年电影史的意大利,却没有在纪录片领域形成可以与其它派别一较高低的相关传统,例如,格里尔逊的英国纪录电影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鼓励重建电影产业,保护电影的民族特色,意大利通过了相关法律,法国亦如此。通过这种方式,纪录片(以及新闻电影杂志)得到各方援助:事实上,法律规定在放映每部故事片的时候,都要搭映纪录片,作为娱乐的“文化”附加项;国家分配了固定的资金支持纪录片,展映纪录片者一律免税;奖金丰厚的“质量奖”颁发给纪录片制片人。这种情况很快导致了投机倾向,产生了大量低质量的影片,并且出现了不成文却极严格的规定:为了不妨碍日常的放映计划和为广告腾出时间,同时,使故事片的放映数量达到最大化,纪录片时长不得超过十到十一分钟(法律已规定了最短时长)。
我本人就能够证明,这种现象是多么荒谬和过分,因为我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职业生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据米歇尔·拉尼的引述,从1950年到1959年的10年中,法国制作的纪录片大约为300多部。而在意大利,仅在1955年,纪录片制作的数量就高达1132部。
伊文思与意大利电影俱乐部
五十年代早期,作为意大利电影社会协会秘书长,我有机会邀请尤里斯·伊文思来意大利展映他的五、六部纪录片。对他而言,这是个访问和了解意大利的好机会。他第一次来意大利佩鲁贾做短期旅行,是在1949年,那时,他是来参加一次国际电影制作者会议,并在会议上做演讲。在电影爱好者们心目中,伊文思的名字极具传奇性,尽管他们当中,几乎无人看过伊文思的任何一部影片。伊文思接受了邀请,并且非常大胆地带着他的五、六部影片来到意大利,其中一部当时还是独家复制版本。1951年春,我陪同伊文思在意大利度过了三个星期,去了很多家电影俱乐部:尽管有许多限制的禁令,但是我们都一一克服,他的演讲和放映获得极大的成功。
当时放映的伊文思的影片有:《桥》、《礁石》《博里纳奇煤矿》和《新地》。访问期间,伊文思还和意大利杰出的导演和编剧会过几次面。虽然旅途奔波,但他对这几次会面非常满意,经常把“我是电影俱乐部之子”这句话挂在嘴边,意指他在20年代欧洲电影联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次意大利之旅,也给伊文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在第二部自传《一种目光的记忆》中,花了几页的篇幅,回忆了一些旅行中发生的有趣事件。以下我仅摘录了其中几小段:
在我生活在铁幕(Iron Curtain)后与世隔绝的那段日子里,为期三周的旅行为我打开了意大利之门。……意大利和意大利电影给了我启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与我的作品如此接近,所以,它拉近了我和意大利导演们的距离……对于我的两部作品《博里纳奇煤矿》和《西班牙土地》,他们说:“你的电影是基础。”对我来说,是战后的意大利人给我上了一堂电影课。……从我到意大利第一天起,就觉得这里的人非常随和,容易亲近。他们热情、坦率,就跟自己人似的接待了我。……在意大利,我找到了轻松、生命的艺术、坦诚、友谊,这些都是我性格中缺少的。在这里,我和人们建立了稳固而长期的友谊。……还有维尔吉利奥·托西(Virgilio Tosi),另一个永远的朋友。他是电影爱好者俱乐部(ciné club)的负责人,陪着我走完令人痴迷的意大利之旅,十五场演讲,包括罗马,佛罗伦萨,的里亚斯特,威尼斯,帕尔马,里窝那等等。电影爱好者俱乐部在意大利非常受欢迎,和共产党的文化协会非常相近,因此,这次旅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新闻报道也给了很大的回应,很快,我的作品被“电影人”和爱好者所熟知。
[1]
1951年,当伊文思离开意大利时,正值冷战时期,所以,他担心他的一些影片会从此消失,或者被埋葬在电影资料馆里。后来,他正式委托意大利电影俱乐部联盟,复制一套他的一些纪录片,以确保这些影片将来能够在意大利发行放映。于是,一些意大利电影导演和电影爱好者俱乐部的成员组织了一次募捐,为了能够迅速筹集支付复制35毫米底片所需的大量资金,以使在伊文思电影的胶卷正片被送回之前,复制下所选的影片。
如今,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话题是:关于那个时期伊文思的作品对于年轻的意大利电影制作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观察一些那个时期意大利的一些纪录片,便可以发现伊文思所带来的影响:那时意大利官方和非官方的一些纪录片,得益于伊文思50年代的几部文献汇编影片(包括《胜利的意志》和《激流之歌》)的贡献,还有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在影片《风中玫瑰》(DIE WINDROSE)中的一些片段,可以看出伊文思电影的影响。
伊文思与意大利电视
20世纪50年代晚期,看到了另一次伊文思和意大利纪录电影和电视的重要互动。意大利国家石油托拉斯埃尼集团(ENI)的领导人恩里科·马泰(Enrico Mattei),1962年,在一次飞机事故中离奇死去,意大利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一部重要的剧情片,名为《企业家之死》(IL CASO MATTEI,1972)。1959年,ENI的老总邀请尤里斯·伊文思摄制关于意大利成功发现石油和天然气的三部系列纪录片。所拍摄影片将由意大利国家电视台RAI播放。伊文思在接受邀请之前,稍微犹豫了一下。后来,他同意了,接着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摄制中去,在拍摄中,伊文思获得了作为艺术家自由表达的保证。伊文思的制作组包括4个年轻的意大利电影工作者,帮助伊文思准备剧本,并协助他拍摄和剪辑,后来,这4个人都成了剧情片的著名导演,他们分别是:丁度·巴拉斯(Tinto Brass),瓦伦蒂诺·奥西尼(Valentino Orsini),保罗(Paolo)和维克托里奥·塔维亚尼(Vittorio Taviani)。
伊文思对这个引人注目的项目感兴趣,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方面,这三部纪录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是极具争议的对抗国际石油生产与分配垄断政策(所谓的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同时,意大利是个充满矛盾、拥有大面积贫穷地区的国家,但是,它又竭尽全力创建现代工业,使其跻身于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个项目给伊文思提供了一个记录意大利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机会。另一方面,伊文思对将要面临的新职业的挑战,深深吸引了他,大量的制片资源供他任意使用,这使他能够切身感受新的电视语言。
现在,我不可能详细描述影片《意大利不是穷国》的漫长摄制过程,当埃尼集团(ENI)不再拥有政治地位来强迫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播放由伊文思准备的这三部影片的电影版本时,对这几部影片的处理充满了戏剧性的结局。电视台只是同意播放那个被广泛审查和经过处理的版本。那时的审查制度非常苛刻(或者由专门审查电影和纪录片的官方机构执行,或者由电视节目组内部的审查机构执行)。伊文思的情况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通过律师的斡旋,伊文思确保了这些影片的放映,被描述为来自“尤里斯·伊文思电影的片段”,而且,影片的放映也被安排在1960年7月深夜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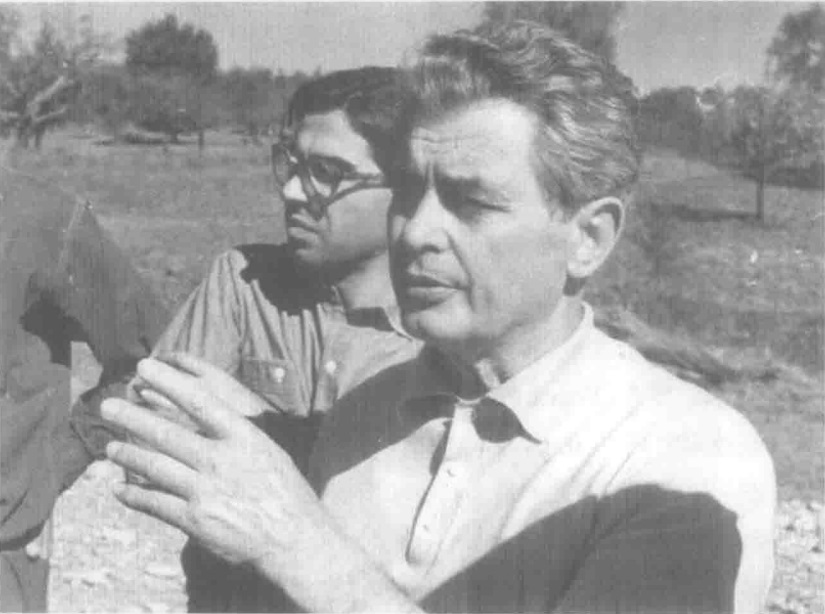
保罗·塔维亚尼与伊文思在《意大利不是穷国》拍摄期间

《意大利不是穷国》剧照
很多年来,我们都以为《意大利不是穷国》的完整版本已经在意大利丢失了。我在罗马国家电影学院授课期间,曾经给学生放映过尤里斯·伊文思这部影片的英文缩减版,这是由RAI电视台处理过,并销售海外的那个版本。而当我的一个学生打算重现伊文思在意大利所拍摄影片的丰富故事作为他的研究内容时,这位学生,也就是斯特凡诺·米西奥(Stefano Missio)的研究表明:伊文思的一个助手曾秘密地邮寄了一份伊文思所制作的原始的、完整版影片的拷贝(放在法国大使馆外交邮袋里)给法国电影资料馆。如今,作为纪录电影史的一部分课程,我们有幸能够放映这个电影的完整版。当我第一次观看这部影片时,我惊奇地发现,在影片结尾的一个段落中,伊文思编入了一段科学的影像素材,而这几个场景的素材,则来自于我制作的一部关于核物理的纪录片。
尤里斯·伊文思制作的这部影片,有着广泛的内容和变化多端的形式,这部由意大利出品的《意大利不是穷国》,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情:该影片是受委托摄制的,但是,赞助商却并不干预伊文思所要求的影片在表达上的自由。于是,无论是埃尼集团的总裁马泰,还是石油托拉斯的管理人员,都不能删除影片中他们不喜欢的场景(如:影片中那个孩子梦见自己能飞的科幻片段)。
伊文思有权利决定该片在形式和主题上,进行一系列不同的表现风格的试验:有时模仿电视的现场直播,在讲述科学的场景中利用动画,充满幽默讽刺,甚至使用非职业演员搬演一些虚构的小故事,并与纯纪录片的片段混合在一起。该电影本来是关于意大利发现石油和天然气的,但伊文思并没有受委托电影的限制,而是将表达的视野延伸到对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分析上,他希望能将信息传达给意大利的子孙后代。遗憾的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的观念看起来有些陈旧,影片的观念完全限定在30、40年前非常流行的一个坚定信仰:对大规模工业化(体现在影片中,一些选址距离威尼斯城非常近的高污染的大型工厂的片段)缺乏环境意识;天真地相信未来的科学能救助人类(观看影片中那位民谣歌手,视战争和核武器为恶魔的片段,但影片指出,对核能的和平应用,将会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进一步分析伊文思这部影片,可以看出他的那几个意大利助手对影片的贡献(尤其是在塔维亚尼兄弟的事例中),这在电影的某些部分中显得格外重要。在当时,伊文思和塔维亚尼兄弟之间有着深刻的互相影响:伊文思接受了他们创造性的帮助,而使该片非常接近虚构片;同时,受伊文思的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放弃他们作为纪录片制作者的工作,而转向他们擅长的虚构片。
最近的伊文思百年诞辰(1998年)纪念活动,提供了在荷兰奈美根和意大利(罗马、托里诺、皮蒂利亚诺和佛罗伦萨)特别放映最初的未删减版的《意大利不是穷国》的机会。如今,这三部系列片仍不为人熟知,即使是对于那些研究伊文思作品的学者。尽管影片的某些部分让观众认为是陈词滥调,但影片的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与伊文思50年代早期在东欧拍摄的作品相比,这三部影片的表现形式十分有趣,主题叙述的结构也展现了伊文思意识形态的辩证演进过程。
当伊文思第一次使用电视语言时,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三部系列片的长度(近两个小时),能够使各种拍摄风格结合使用,包括重复利用各种来源的影视资料。
伊文思这部命运多舛的影片的拍摄及其后期制作的故事,肯定值得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从几个版本的比较开始研究:由伊文思制作的未删减版本与在意大利播放的支离破碎的摘录版本进行比较;伊文思准备的但根本没有影院放映的版本与意大利电视台处理过的,误导地利用了伊文思的名字而销售给海外的版本进行比较。与影片《意大利不是穷国》有关的、尚未公开出版的重要文献保存在伊文思欧洲基金会的档案馆里,同时其它资料都已经公诸于世了。而对于纪录片《意大利不是穷国》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此,我引用一封写于1959年12月17日罗马的长信,这封信是负责EM电影出品的PROA电影公司总裁瓦利(Valli)先生写的。该信是寄给距离罗马很近的一家伊文思和他的意大利同事们工作居住的宾馆。写这封信是瓦利想立刻通知伊文思,在前一天晚上意大利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关于海湾石油公司在西西里岛首次发现石油的纪录片。瓦利在信里还说了一些他对该节目意义的评论,为他在法国所犯的错误辩解:
……那是美国的垄断:那是和马泰以及他的“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观念争论的一个主要方面。这部电影非常糟糕,解说笨拙而错误。影片讲了太多关于马泰领导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斗争的重要性。很显然,这次放映已经在这几天结束了,因为EM相关的影片还没有完成;同时,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在政治上你也不要忽视这个争论的答案。我们一定会想,马泰必须和盘托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付了钱,而且是因为那个时间,他不能让其它的晚间节目在电视上播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电视是被他的对手所垄断的。
[2]
另一份有趣的文件,是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也是瓦利发的)是1961年4月14日发给当时正在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伊文思的(那时,伊文思已经很遗憾地结束了他的意大利电影摄制)。为了回应尤里斯·伊文思多次抗议意大利电视台未经他本人授权,就在处理过的电视版本《意大利不是穷国》上使用他的名字,而且伊文思并没有收到全部重新编辑他的拷贝的要求,瓦利发了这封电报给伊文思:
我们会保护你的名字和声誉,因为与电视版本相比,好莱坞版本比电视台版本更接近你的原始版本。停止使用你的片名,就表明停止从尤里斯·伊文思的影片中提取电视片。原始版本并没有在意大利通过审查,也没有获得出口执照。这就是你的拷贝还留在罗马的原因。祝好!瓦利!
1961年7月末和9月初之间,伊文思写了一封信给瓦利,从这封信的草稿(至少有两份手写的草稿)中的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我上面所引用的这些简短的片段:
亲爱的朋友,近来可好?收到你的信已有一段时间了。一年多来,我们只是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里互相发了几封电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在1960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以及其他地方,我们的电影《意大利不是穷国》都非常地激动人心。我摄制了这部由3部分构成的影片(每部约45分钟),他们迫使我们将电影剪短甚至滥用这部电影,这些行为都破坏了这部影片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些滥剪是在反动当局以及那些缺乏艺术细胞的人要求下进行的。我倍受侮辱,我对他们破坏我作品的行为感到愤慨。我的作品是以纯粹的思想,诚实的态度拍摄的,表达正确,一开始每个人都已经接受了它。在您以及您的制作公司的帮助下,我完成了这部电影,我为此感到十分自豪。
[3]
《愚公移山》与意大利电视台
20世纪60、70年代,伊文思有许多机会访问意大利。有一次,作为一种神话般的报应,试图破坏《意大利不是穷国》的RAI电视台,决定购买和播出片长12小时的《愚公移山》系列纪录电影。这是因为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1976年,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领导的意大利共产党变得十分强大,在意大利各大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委员会,它的独立政策是针对东欧的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意大利国家电视公司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愿意引进并播出《愚公移山》,而且签订合同,邀请尤里斯·伊文思和玛瑟琳·罗丽丹来罗马监制该系列片意大利版的筹备工作。事实上,像意大利这样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配音技术的国家,让一个外国的纪录片导演来选配音演员,以及决定原版声轨和意大利版声轨之间的混音水平是很奇怪的事情。即使对于那些已获许多奥斯卡奖的好莱坞影片的配音,或者在影院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影片来说,对待伊文思的《愚公移山》的这种情况都是罕见的。
1977年,影片《愚公移山》刚刚制作完成在影院上映,但是,我们应该记得,60年代,在伊文思访问意大利期间,伊文思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还被要求立即出境。这事发生在1965年末的佛罗伦萨:
我们带着法语版的电影《天空与土地》,在最后一刻抵达。意大利的波波里电影节
[4]一直非常渴望得到这部影片。那时,正值越南战争期间。不幸的是,警方得知这部影片到了佛罗伦萨(没有官方许可证)。他们遂想将我驱逐出境,很快又撤销了这个决定。尼
[5](Nenni)亲自干预了此事。意大利电影导演,包括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表现了他们的团结精神,他们集体宣称,官方质疑我的举动是愚蠢的。最后,我收到了官方的道歉。
[6]

1977年,维尔吉利奥·托西与伊文思在罗马的纪录片研讨会上
后来,1985年,意大利总统授予尤里斯·伊文思“意大利共和国高级勋章”。
伊文思教授
1977年秋,当伊文思来到罗马监制意大利版的《愚公移山》时,他已是79岁高龄了,但他身体很好。那时,我已经在罗马的实验电影中心(Centro Sperimentale dj Cinematografia)开始教授纪录片方面的课程。这个实验中心现在改名为意大利全国电影学院。世界上第二古老的电影学院。凭着我们多年来的深厚友谊,我斗胆问伊文思是否愿意来电影学院做一次3小时的研讨会。他十分热情地答应了。
研讨会非常成功。有些学生还用非标准的半寸磁带机把它录下来了。1998年,为了纪念伊文思的百年诞辰,人们决定尝试通过更现代的技术来复原老版的磁带。复原工作至今未完成,因为声轨已破烂不堪,但是,其中一个学生制作了一段四十分钟的摘要,在参与那次讨论会的过程中,为了把伊文思介绍给学生以及翻译他们的对话,二十多年后,我发现,通过老式的黑白画面来再现往事,并且在庆祝伊文思百年诞辰期间(第一次是1998年11月,在意大利的皮蒂利亚诺,托斯卡纳,第二次是1998年12月,在奈美根的国际座谈会上)呈现部分未发表过的视听材料,这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伊文思与“佛罗伦萨”放映
在我简要地综述伊文思与意大利纪录片之间的关系时,我想提醒大家注意,1979年,为了庆祝尤里斯·伊文思历经50年的电影生涯,意大利的两个城市(摩德纳和佛罗伦萨)分别举办了伊文思电影回顾展和展览会,这次活动是由荷兰电影博物馆组织的。这些活动为伊文思的第一部自传(《摄影机和我》)意大利文版的出版提供了机会。此外,佛罗伦萨的权威人士以及托斯卡纳当地政府,邀请伊文思筹拍一个关于佛罗伦萨的纪录电影项目。后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也参与了该项目。
尤里斯·伊文思和玛瑟琳·罗丽丹在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待了几个星期,配了一个职员帮他们做事。最后,他们写出了一个40页左右的剧本,该剧本提交给了托斯卡纳地区政府。遗憾的足,由于官场政治的复杂性,该项目成为互相“推卸责任”的牺牲品。因此,这个剧本是一个原则上被接受的,但没有实质性结果的项目。
最近,值此百年纪念之际,佛罗伦萨组织了一次圆桌会议来讨论当年的这个项目。会上,人们对这份标注日期为1981年春的剧本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讨论了这个剧本中许多十分有趣的观察和评论,尤其是剧本中描述这部影片的想法,是以非常原始的电影语言和电视语言的混合使用为基础,主要意图并不是要摄制一部关于佛罗伦萨的纪录片。在伊文思第二本自传(1982年)的最后,他写道:
明天,当我前往佛罗伦萨去摄制一部新影片时,那里将是另一个舞台。或许这是我最后的影片?……我想象这部影片是关于一位年老的纪录片导演和一个城市的相遇,并在这个城市里体验了许多东西。关于他自己的每一个故事,那里的博物馆,那里的富饶,以及它们的记忆。这是一个镜像游戏,一个双重的疑问:一个人想要抓住现实中这个城市的男人;而这个城市却质问这个拍摄它的人。这是一场斗争,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了。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最终,对于一个电影工作者来说,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7]
伊文思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已是83岁高龄了,但却充满青春的热情。在这个关于佛罗伦萨的剧本中,他以同样的热情,回忆了1951年他第一次邂逅这个城市的情景,也就是那时,他为了能够在当地的电影俱乐部放映他的影片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的情形。
[1] 伊文思,罗伯特·戴斯唐克:《一种目光的记忆》,1982年,巴黎,第247-250页。
[2] 手稿存于荷兰奈美根的尤里斯·伊文思档案馆。
[3] 手稿存于荷兰奈美根的尤里斯·伊文思档案馆。
[4] Popoli电影节是国际上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成立于1959年,主要举办地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倡导以“真实视觉记录”的方式展示人类学和社会学而闻名,有“纪录片界的戛纳”的美誉。——译者注
[5] Pietro Sandro Nenni,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反法西斯战士。
[6] 1989年3月18日,Andrea Vannini对伊文思的访谈,发表于1989年3月22日的“La Repubblica”。
[7] 伊文思,罗伯特·戴斯唐克:《一种目光的记忆》,1982年,巴黎,第344-345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