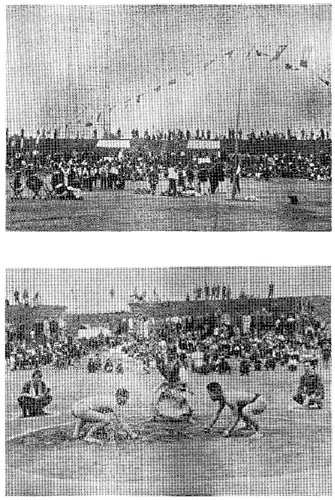“他(柴田)的独特之处,就是他决不独断专行。在开展倍增运动之前,他做了这样一些准备工作:尽管高津派已经脱离了俱乐部,但一些从和工会时期就入会的老会员认为,随着俱乐部逐渐大众化,它的阶级觉悟也在逐步流失,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招来的新会员连寻职会和俱乐部之间的区别都说不出来,那么,发展新会员和加强俱乐部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老会员到处进行争论,让新的活动家们十分困惑。
“新年会的举办地点,特意选在立石的坂村氏家中。在宴会上,年轻的活动家与看上去像是前辈的人坐在一起,听大家讨论关于发展群众组织的原则,以及由辩证地掌握质与量的问题而生的唯物辩证法,再以此为契机学习这些问题。通过这种方法,使大多数人形成了对高津氏等人的明确的批评意见,促使他们理解了倍增运动的意义,加强了他们对这项工作的信心。每当柴田做出重大决定时,他就会通过这种方法,让活动家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好准备。”
“昭和十四年夏天,我们家从新婚后住的房子里搬到了江之岛的海之家。柴田先生对我说:‘你结婚后身子就不太好,去了江之岛的话,身子应该会好一点的,你就去那里吧,悠着点就行。’话是这么说,可是在那边根本没时间休息。那两个多月里,白石要坐火车到位于芝区的钻石印刷公司上班,到了周六和周日,就会有来自各个工厂的大批工人过来,我得跑来跑去,帮他们做饭、泡茶。”
“有一次,我在俱乐部办公室里,看到了柴田氏是怎么对待年轻人的,这让我非常佩服。那次好像是京桥支部和神田支部的代表为了哪个支部能在星期天使用海之家而争了起来。从一开始,柴田氏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做出结论,立即让争论停下来。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耐心地让双方说出自己的意见、让双方讨论。双方争着争着就有些激动了。然后他就劝了一两句:海之家不是单纯的娱乐场所,而是全体印刷工人的重要的休养设施。于是双方都冷静下来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我以前在参加安布论战(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时,为了排除无政府主义者,总是急急忙忙地得出结论,但是,还是应该让大家自己决定才对。我住在海之家的时候,那里也对工人进行教育。记得有个同盟社
[43]的记者讲了国际形势。他讲了西班牙、法国、德国、巴尔干和北欧三国的地理,还讲了日本和美国的地位,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还对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与日本工人运动的差异做了专门的说明。有人就问,为什么日本会是这个样子呢?记者自然就解释说,日本的天皇制是如何跟资产阶级与地主勾结、如何剥削日本人民的,这时候柴田氏就劝记者不要讲了,‘剩下的还是改天再讲吧。’我们并不能确定来海之家的都是什么人
[44]。在那种情况下,他仍然不急于鼓动、而是把踏实地培养年轻人当作当前要务,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活动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推进的,而不是要进行自发的联谊。我当时因为参加全协的活动被判了缓刑,但是,俱乐部关于运动的想法,却与我不谋而合,这让我非常感动。”
“我在征兵体检中原先被列入乙种第二等
[46],但是马上又被编入乙种第一等,当年(昭和十三年)十一月被征召入伍进行训练,次年退伍,但是没过多久又被重新征召,部署在中国山东省。然而好像是由于不需要替补人员,不到半年我又退伍回家了。我先在中屋三间印刷干,但我嫌那里工钱太少,很快就跳槽去了神田的三秀舍
[47]。但三秀舍那里有许多由养成工
[48]转来的拣字工,总是催我干活,可是工钱也不多,所以我就不上班了,到巢鸭
[49]的康文社和小石川的常盘印刷等公司去碰碰运气,结果都不怎么样,不管哪里都是一个样。
“一想到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就很窝火,有一天午休,我正在沉思的时候,杉浦正男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虽然我跟他在同一个拣字车间工作,但他排九点
[50],我排八点,不在一个地方干活,所以没跟他说过话。但我知道他是出版工俱乐部的干部,经常看见他跟工头顶嘴,那个工头总是坐在宽大的拣字车间正中央的一张大桌子前,气势汹汹地冲我们大吼大叫,但杉浦却面无惧色地向他提出抗议或申诉,我从装活字的箱子后面看见他这样做的时候,都觉得既害怕,又很佩服他。
“我就断断续续地把自己的想法都给讲了出来。我现在不记得杉浦当时说了什么,但他的结论是劝我打起精神,给俱乐部帮点忙。跟杉浦同样排九点字体的铃木幸一
[51]君也过来给我打气鼓劲。
“当时出版工俱乐部神田支部是按照地域分成东西两片开展组织工作的。东边是以三秀舍为中心的一块地方,位于从国电
[52]的神田站到都电的神田桥、小川町再到国电的御茶水站一线的内侧,包括活文社、明治印刷、宫本印刷、秀英社等十三家印刷工厂,这一带的发展会员、联络等工作是由杉浦牵头搞的,铃木幸一君也给他打下手。西边的组织工作的领头人是小宫吉一,他的助手还有大桥宏荣、南云富吉
[53]等人。
“联络其它工厂的会员、发放机关报、收集会费、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批量购买、分发工作用的草鞋和遮阳帽
[54]等物品,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午休的时候做的,为了最有效地利用午休时间,午饭的便当都是放在装活字的箱子后面,在工作时间偷偷吃掉,午休的钟声一响,就马上跳上公司的自行车,飞驰而去。
“各公司都开始成立产业报国会的时候,三秀舍也经常叫全体员工到印刷工厂集合,听社长岛连太郎的儿子岛诚训话。岛诚这个人以前在上帝大
[55]的时候,曾经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遭受了残酷的拷问后转向了,因为拷问,落下了面部神经痛的后遗症,说话的时候脸部经常抽搐。
“岛诚打算在产业报国会三秀舍分会里成立青年部,为此向杉浦提出了同俱乐部的年轻人谈一谈的建议,杉浦、铃木、佐藤商量之后,决定由我和铃木幸一带头,去跟岛诚会谈。当天晚上,有大概八个青年拣字工出席了会谈,为首的是来给俱乐部帮忙的野泽惠意一
[56]君。岛诚提起了成立青年部的事,并向大家征求意见。
“这是我们头一次参加会谈之类的玩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们啥都说不出来,对方又是社长的少爷,又有学生运动的经验,所以我们谁都不敢开口。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只好鼓起勇气说了几句:‘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接受自上而下地强制成立青年部、自己却毫无自主性的做法。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至少请让我们自己来成立。’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岛诚盯着我的脸,说了一句‘让你们自己来?’,露出了嘲笑似的表情,然后就什么都不说了。成立青年部的事儿也就搁下了,不久后岛诚死了,这个主意就再也没人提起了。
“当时神田支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水道桥站附近的白石光雄的家里。虽然立着‘天鹅咖啡店’的招牌,但我在那里的时候,楼下的椅子什么的都倒过来放着,就好像已经关店一样。晚上加完班以后,或是在不加班的傍晚闲逛的时候,我经常到二楼跟小宫吉一讨论。当时我信神佛——虽然并不虔诚——对于我的唯神论和唯心论,小宫总是耐心地听我讲,再用具体事实来劝说我。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不再进行这样的讨论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后,不得不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再也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事了,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变成了跟活动有关的各种问题。我第一次见到田口俊郎,也是在咖啡馆的二楼,那时他穿着立领学生服,显得很精悍。白石的妻子阿圣也是在这时候怀上了长男一雄
[57]君,挺着大肚子。
“杉浦负责芝支部一带的活动,东神田的活动就由铃木幸一和我牵头搞,所以我充满了干劲,每天晚上都要到办公室去,跟小宫、南云、大桥等人的关系也变得密切了。一天晚上,小宫他们说‘找到了一个人才’,不由分说地把那个人拉来了办公室,他就是渡边武
[58]。他当时在精兴社工作,拣字技术好,又写得一手好俳句。于是我们又多了一位新活动家。”
“下班后,绝对不要一个人回家。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回去。在工厂里,如果有人诉苦,要注意倾听。可以的话,把那个诉苦的人带到办公室来,让他畅所欲言。还有,在要开展组织工作的工厂里,要对核心人物集中开展工作。中屋三间印刷有个酒井贡
[77],他是公司里技术最好的技工。公司在制定计件工资率的时候,都是先让他干活,再根据他的效率来决定计件工资率。他的技术很好,所以很受工人信赖。他得盲肠炎的时候,俱乐部的所有人都积极援助他。所以他加入了俱乐部。他加入俱乐部之后,俱乐部会员在中屋三间印刷的影响力也随着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