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杜章智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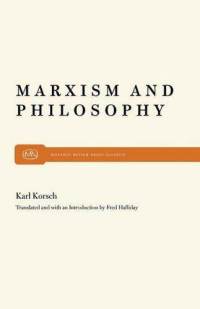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192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第11年卷〔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1. Jahrgang, 1923〕,同年晚些时候出版了单行本〔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C. L. Hirschfeld, 1923〕。本译文选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辑,第241—257页;1988年第2辑,第223—241页;1988年第3辑,第201—215页。译者根据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1930年莱比锡德文第2版和1970年纽约英文版〔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Hirschfeld, 1930;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译出。原译文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现改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部分引文依照相应《全集》和《选集》进行了修订,部分人名进行了修订。文末附有录入者制作的部分译名对照表,收有文中涉及的部分人名、书名、刊名的原文。
| 我们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1] 列宁,1922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
直到最近,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很少了解,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中可能包含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哲学教授看来,马克思主义顶多是19世纪哲学史叫作“黑格尔学派的瓦解”一章中的很小的一小节。[2]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怎么重视他们理论的“哲学方面”,虽然原因完全不同。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很自豪地指出,在历史上,德国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3]但是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主要是“哲学”。[4]相反,他们认为,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彻底地克服和“扬弃”不仅以往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所有一切哲学。下面我将要较详细地说明,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见解,这种克服和扬弃是或者应该是什么性质。暂且我只记录下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对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个问题简直不再是什么问题了。他们对待哲学问题的方式,完全可以用恩格斯有一次在谈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时使用的生动语言来描述: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随便撇在一旁”[5]。事实上,后来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非常正统地遵从大师们的教导,以完全同样随便的方式不仅对待黑格尔哲学,而且对待一切哲学。例如,弗朗茨·梅林不止一次言简意赅地这样描述他自己对哲学问题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同意“拒绝一切哲学幻想”,这是“大师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获得不朽成就的前提条件”。[6]这句话出自一个能够有权说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详细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起源”的人之口,它对第二国际(1889—1914)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在一切哲学问题上一般占支配地位的立场说来是极其典型的。那个时期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研究甚至基本上不是狭义哲学的问题,而只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关的问题,至多看作是完全浪费时间和精力。当然,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都许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讨论这种哲学问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亲自参加。但是他们在这样做时明确表明,这种问题的解释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完全无关,而且必将永远是如此。[7]然而这种见解只是在下面这种前提下才是不言而喻和在逻辑上合理的,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完全不能改变,而且不包含对任何哲学问题的任何特殊立场。这意味着,例如,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私人哲学生活中成为亚瑟·叔本华的追随者,不能看作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期,不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的矛盾多么大,在这一点上,两个极端之间却有着明显的一致。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相互保证,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而且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相互保证,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说来与哲学毫不相干——而且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然而从这同样的基本立场出发的还有第三种倾向;在整个这一时期内,这是唯一多少比较关心社会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倾向。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好谈哲理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以一般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康德、狄慈根、马赫或任何其他哲学的思想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体系。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明确表明了,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本身也缺乏哲学内容。[8]
今天很容易表明,我们发现无论资产阶级学者还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都一致持有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纯粹否定的看法,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分析非常肤浅和不完整而产生出来的。然而,他们双方得出这个结论时所处的条件有一部分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我要把他们分开来描述。这样就会看得很清楚,尽管双方的动机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组原因在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吻合的。在19世纪下半叶的资产阶级学者那里,由于完全忘却黑格尔哲学,因而完全失去了对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辩证”考察,而这在黑格尔时代是全部哲学和科学的活的原则。另一方面,在这同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同样地越来越忘却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40年代离开黑格尔时,正是完全有意识地把它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出来,并且把它转用到对历史社会发展过程的“唯物主义”观点上来。[9]
我先来简略地谈谈,为什么从19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越来越放弃哲学思想史的辩证观念,并且因此不能在19世纪哲学思想总的发展的范围内来适当地分析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本质及其意义。
人们可能会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忽视和错误解释有更直接得多的原因,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用辩证法的被放弃来解释它的状况。的确,在19世纪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写作中,马马虎虎对待马克思主义,甚至也同样马马虎虎对待像大·弗·施特劳斯、布·鲍威尔和路·费尔巴哈这样的资产阶级“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无可否认地是由于有一种自觉的阶级本能在起作用。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指责资产阶级哲学家有意识地把他们的哲学或哲学史从属于阶级利益,那么我们就只会把这里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当然有符合这种简单设想的事例。[10]但是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哲学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马克思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专门论述了这类相互关系。他在那里说,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由各种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1]。在这种意义上“由阶级决定的”、然而离它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特别遥远的一部分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阶级的哲学。从其内容来看这是最明显的,但是这归根到底也适用于它的形式方面。[12]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完全不懂这一现象,并且是从马克思的意义上,即“唯物主义地因而也是科学地”[13]去真正理解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满足于用它的“世俗的核心内容”(即阶级意识和它“归根到底”掩盖着的经济利益)来对它作出直接的、没有任何中介的解释。我们的任务是详细说明,究竟是哪些中介因素使那些甚至真心诚意要最“客观地”研究“纯”真理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或者只能以很不适当的和肤浅的方式来解释它。对于我们的目的说来,这些中介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哲学史,由于社会经济原因放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方法,回到了一种使得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现象中搞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的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方法。
在出自资产阶级作者之手的对19世纪哲学史的一般描述中,在某个地方有一条很深的裂缝,如果说能克服的话,也只有以极其矫饰的方式才能克服。这些历史学家想要以完全意识形态的和彻底非辩证的方式把哲学思想的发展描述为纯粹的“思想史”过程。因此不可能看到他们怎么能够为下述事实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即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宏伟的黑格尔哲学还是连它最激烈的敌人(叔本华或海尔巴特)也不能避开它的强大的精神影响,可是到19世纪50年代,它在德国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追随者,不久之后就完全不再被人所理解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去设法提供这样一种解释,而是满足于在他们的历史中在“黑格尔学派的瓦解”这一纯粹否定的标题下记下黑格尔逝世后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的内容是很有意义的,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有极高的正式的哲学水平。这些争论发生在黑格尔的不同倾向(右派、中派以及左派的不同倾向,特別是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这些哲学史家简单地为黑格尔哲学运动安排了一种绝对的“终结”来结束这个时期。然后他们就用回到康德(赫尔姆霍茨、泽勒尔、科布曼、朗格)来开始19世纪60年代,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代,与任何别的东西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类哲学史有三大局限性,其中有两种可以通过一种本身多少完全停留在思想史领域内部的批判审核揭示出来。的确,最近几年来有一些较彻底的哲学家,特别是狄尔泰和他的学派,已经在这两方面可观地扩大了一般哲学史的受到限制的视野。因此,这两种局限性可以被认为已经在原则上被克服了,虽然在实际上它们到今天还存在着,也许还要继续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然而,第三种局限性无论如何不能从思想史领域内部来克服;因此它至今甚至在原则上也没有被当前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所克服。
19世纪下半叶的资产阶级哲学史的这三种局限性的第一种,可以描述为“纯粹哲学的”局限性。当时的意识形态家没有看到,包含在哲学中的思想不仅在哲学中,而且在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中也能同样好地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这种过程正好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就大规模地开始了。第二种局限性是“地域性的”局限性,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哲学教授那里表现得最典型:这些尊贵的德国人忽略了在德国的国境之外还有其他的“哲学家”。因此,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他们都完全看不到,黑格尔体系虽然在德国已被宣布死去几十年了,但是在国外的一些地方,不仅是它的内容,甚至作为一种体系和方法都一直在继续盛行。在最近几十年的哲学史发展中,哲学史视野的这头两种局限性基本上已被克服,上面描绘的19世纪下半叶德国一般哲学史的景象近来已大大改观。然而,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不能克服他们哲学史认识的第三种局限性,因为这要求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放弃那种构成他们全部历史和哲学科学的最本质的先验性的资产阶级阶级立场。因为19世纪哲学看起来是纯粹“观念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只有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到全面和根本的理解。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在他们发展的现阶段不能无所顾忌和无条件地进行研究的正是这种联系。
这说明,为什么19世纪哲学总发展中的某些阶段直至今天对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说来还必须依然是“超验的”东西。这也说明,为什么在今天资产阶级哲学史的地图上还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些引人注意的“空白点”(黑格尔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的“终结”,在那以后和哲学在19世纪60年代“重新复苏”以前出现的空白)。这也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哲学史今天甚至对那个它们以前曾完全正确地理解了其具体本质的德国哲学的时代,也再不能正确和全面地理解了。换句话说,无论是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思想发展,还是在那以前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都不能仅仅作为一串思想来理解。这个在历史书中通常被叫作“德国唯心主义”时代的哲学思想的伟大时期,只要人们在考察它时完全忽略或者只是皮毛地以事后追忆的方式注意到那些对这种哲学发展的全部内容和过程极为重要的联系,要想了解它的本质内容和全部意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联系就是这个时期的“精神运动”和与它同时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及其他著作中,有一些章节描写他的直接先行者——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的本质,这些章节对于所谓“德国唯心主义”的整个时期,包括它的圆满“结尾”即黑格尔体系本身在内,都是适用的。它们也适用于后来19世纪40年代在黑格尔学派不同倾向之间的冲突。黑格尔写道,在这个彻底革命的时代的各种哲学体系中,“革命是通过思想的形式概括出来了、表达出来了”。[14]从黑格尔随后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这里说的不是今天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喜欢叫作思想革命的东西,即不是那种远离现实斗争的粗疏领域而在书斋的纯粹领域中安安静静进行的过程。这位由资产阶级社会在其革命时期产生出来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把“思想形式的革命”看作现实革命的总社会过程的一个客观组成部分。[15]“世界历史上这一个伟大的时代(其最内在的本质将在历史哲学里得到理解),只有两个民族,即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互相反对的,或正因为它们是互相反对的。别的国家并没有参加到里面来,虽说它们的政府以及它们的人民在政治上参加了,但不是在内在精神上参加了。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涌现出来。这个原则出现在德国现实生活中,显得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暴力和对于这种暴力的反动。”[16]在几页以后(第501页),当他在论述康德的哲学时,黑格尔又回到这同样的思想上来:“卢梭已经把自由提出来当作绝对的东西了。康德提出了同样的原则,不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提出来的;法国则从意志方面来掌握这个原则。法国人常说:‘他头脑发热’(Il ala tête pres du bonnet);意思是说,法国人具有现实感、实践的意志、把事情办成的决心,——在他们那里观念立刻就能转变成行动。因此人们都很实际地注重现实世界的事务。尽管自由本身是具体的,但自由在被他们应用到现实世界时却仍是未经发展的、带着抽象性的。要想把抽象的观念生硬地应用于现实,那就是破坏了现实。人民群众把自由抓到手里,所表现出来的狂诞情形实在可怕。在德国,同一个自由原则占据了意识的兴趣;但只是在理论方面得到了发挥。我们在头脑里面和头脑上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是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生于哥尼斯堡”,等等。黑格尔著作中的这些段落实际上说出了那使得世界历史的这一伟大时代的最内在本质变得可以理解的原则: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另一处,黑格尔以更一般的方式提出了这一原则,他写道,每一种哲学都只能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自己的时代”。[17]这个原则对于真正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无论怎样都非常重要,而对于社会生活发展的革命时期说来就更加切合。的确,正是这一点能说明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所遭到的沉重厄运。在19世纪中叶,这个阶级在其社会实践中不再是革命的了,而且由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它也从而失去了在思想中把握观念和现实历史发展之间、首先是哲学和革命之间的真正辩证的相互关系的能力。在社会实践中,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展在19世纪中叶衰退和停止了。这个过程在哲学发展的明显衰退和终止中得到了它的意识形态表现,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至今还在论述这种情况。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宇伯威格和海因策的评沦,他们在他们著作有关章节的开头说,哲学在这个时期处于“一种普遍衰竭的状况”,“越来越失去对文化活动的影响”。按照宇伯威格的看法,这种可悲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心理上突然变化的倾向”,而一切“外部因素”只有“次要的作用”。这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向他自己和他的读者这样“解释”这些“心理上突然变化的倾向”;“人们对夸夸其谈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辨都厌倦了(!),要求有更带实质性的精神食粮。”相反,如果坚决而彻底地用辩证的方法,甚至是用黑格尔用过的那种不发展的、只是部分意识到的形式(也就是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来看待19世纪的哲学发展,那么这种发展立刻就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甚至从思想史的角度也会显得更加丰满。
从这个观点看,思想领域的革命运动不是在19世纪40年代逐渐消减和最终停止了,只是经历了一次深刻而重大的性质变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的德国古典哲学不是终结了,而是转变成为一种以后在思想史上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的新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提出和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直至今天或者完全忽略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种本质的和必然的关系,或者只是不全面地和错误地理解和描述了这种关系。为了正确而全面地理解这种关系,必须拋弃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史家通常使用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方法,而采取一种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一定是辩证的立场,无论是黑格尔意义上还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辩证都可以。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立刻就能不仅看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看到这种相互关系的内在必然性。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它们在思想史上(即在意识形态上)相互之间所处的关系,应该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社会和政治实践领域所处的关系一样。是在同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产生出“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另一方面新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地”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相对抗。这一切过程相互之间发生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按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只是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产生的“另一面”;两个面合在一起才构成历史过程的具体整体。
这种辩证的观察方法使我们能够把上面提到的四种不同的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四个环节。这使得我们能够理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制定的、构成无产阶级独立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的那种新科学的真正本性。[18]这种唯物主义哲学是从革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先进体系中产生出来的;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哲学史或是完全忽略了它,或是只能从否定的和真正颠倒的意义上理解它的本性。[19]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实践目标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内部是不能实现的。同样,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不能理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独立和自觉表现的那些一般原理的本质。资产阶级立场在它在社会实践中必须止步的地方,在理论中也必须止步——只要它不想完全停止成为“资产阶级”立场,即不想扬弃自己的话。只有当哲学史克服了这种局限性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才不再是先验的彼岸,而成为可能的认识对象。然而,使得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问题的任何正确理解大大复杂化的特殊情况是:似乎正是通过这种对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性的克服(这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上崭新的哲学内容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同时就作为一种哲学对象被扬弃和消灭了。
在本文一开始我们就说过,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想要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他们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相反,两人都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密切历史联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社会主义按其内容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无产阶级内部作为其物质状况的结果而必然产生出的新世界观的产物。但是,它通过同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联系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形式(这使它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形式上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产生出来的。[20]当然,这种(形式上的)哲学起源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其独立的形式中和进一步发展中必须仍然是一种哲学。至迟从1845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立场描述为不再是哲学的。[21]在这里应该记住的是,在他们看来一切哲学等于资产阶级哲学。但是,正是这种一切哲学等于资产阶级哲学的意义需要加以强调。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同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反对国家的一种特定历史形式,而且他们历史地和唯物主义地把一般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并且据此宣布消灭国家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目的。同样,他们并不仅仅反对特定的哲学体系,而是要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克服和扬弃一切哲学。[22]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实在论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见解和拉萨尔主义以及其他一切新旧“庸俗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法学家等人的意识形态空话”(马克思语)之间的主要矛盾。后者根本从未越出过“资产阶级水平”,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23]
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任何透彻的说明,都必须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下述这种明确无误的说法作为出发点,即他们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是不仅废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从而同时废除一切哲学。[24]我们不应该以下面这种看法来模糊这种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态度的根本意义,即把这整个争论看作只是一场笔战,也就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给某些在黑格尔术语中叫作“科学的哲学方面”的认识论原则取了一个新的名称,这些原则实际上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时都被保存下来了。[25]当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恩格斯晚期著作中,[26]有一些说法似乎暗示了这种观点。但是很容易看出,哲学本身并不是单由废除哲学的名称而被废除的。[27]这种纯粹名词术语问题,在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任何认真的考察时必须抛在一边。对我们说来,问题勿宁是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在19世纪40年代,但是在以后也多次说到的废除哲学。这个过程应该怎样完成,或者它是否已经完成?通过什么行动?以什么速度?为了谁?是否应该认为这种废除哲学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次脑力行动所谓一劳永逸地完成了?是否应该认为它只是为马克思主义者完成的,或者应该认为它是为全体无产阶级或是全体人类完成的呢?[28]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它(像废除国家一样)看作一个要经过各种不同阶段的漫长而艰苦的革命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这一艰苦过程还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即废除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到底处于什么关系呢?
如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这样提出的话,那就很清楚,我们在这里不是对早已被解决了的问题进行无意义和无目的的思索。相反,这个问题仍然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的确,它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现阶段特别重要。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来的态度是,仿佛这里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至多只有一个对阶级斗争的实践将永远无关紧要的问题。现在这种态度本身显得很成问题,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加以对比,就更成问题。大家知道,这后一个问题,正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的那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29]。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废除国家和废除哲学之间有一定联系,那么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忽视之间是否也有联系呢?问题可以提得更确切一点。列宁对机会主义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尖锐批评,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忽视同一个更一般的背景联系起来。这个背景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问题上也起作用?换句话说,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问题的忽视是不是也和“他们很少注意一般革命问题”有关?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对那在最近十年来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分裂成三个敌对阵营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至今发生的最大的危机的性质和原因,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纯粹渐进发展的漫长时期结束,一个革命斗争的新时代开始了。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中的这种变化,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情况变得很明显,模仿者们的异常陈腐和简单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对它自己的全部问题都了解得极不充分,更不要说对在这以外的一系列问题采取一定的立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最清楚地表现在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这个重大问题,自从1848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以来,从未在实践中严肃地提出过。它由世界大战、1917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以及1918年中央国家[30]的崩溃再一次具体地提上了日程。现在已很清楚,对于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最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消亡”这样重大的过渡和目标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没有任何一致看法。相反,一旦这一切问题以具体的和不可避免的方式提出来,对它们立刻就会出现至少三种不同的理论立场,而且都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在战前时期,这三种倾向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分别为伦纳、考茨基和列宁)不仅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被看作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31]几十年来,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和工联的阵营内有明显的危机;它采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冲突的形式。[32]但是随着对这些新问题的各种不同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情况变得很清楚,这种明显的危机只是穿越正统马克思主义战线本身的一条更深刻得多的裂缝的暂时的和幻想的表现形式。在这条裂缝的一边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改良主义,它很快就同先前的修正主义多少合流了。在另一边,一个新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代表们发动了一场斗争,在恢复纯粹的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口号下既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老改良主义,又反对“中派”的新改良主义。
这次危机是世界大战爆发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发生的。但是,如果把它只是归咎于那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肤浅和贫乏得成为第二国际的正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和政论家们的怯懦或缺乏革命信念,那将是对历史过程的极端肤浅的、彻底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甚至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而是完全非辩证的看法。然而,如果以为列宁、考茨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大论战只是为了通过忠诚地重建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恢复马克思主义,那也同样是肤浅的和非辩证的。[33]至今为止,我们只用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引入历史研究中的辩证方法来分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从它当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进行这种分析的唯一真正“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是把它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从它最初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产生以来的每一次改变、发展和修正理解为它的时代的必然产物(黑格尔)。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设法把它们理解为是由历史社会过程的总体决定的,它们就是这种历史社会过程的一般表现(马克思)。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将能理解马克思主义退化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原因。我们也将能看出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今天如此热情地致力于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努力的含义。
如果我们这样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我们就能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它诞生以来已经经历过的、而且由于这个时代的具体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3年前后开始,在思想史上相当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它随着1848年革命结束——在思想史上相当于《共产党宣言》。第二个时期始于巴黎无产阶级在1848年六月战斗中遭到血腥镇压和马克思在1864年《成立宣言》中出色地描写的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和解放梦“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我们在这里注意的不是整个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而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一般阶级史背景下的内部发展史。因此第二阶段可以说大致延续到上世纪末,一切较次要的小阶段可以略而不提(第一国际的成立和瓦解;巴黎公社的插曲;马克思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工联;第二国际的成立)。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初起直到现在,并将延续到不定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经过这样划分,呈现出下述图景。它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自然在整个后期本质上没有变化,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变的。不管他们如何否定哲学,这第一个表现形式完全浸透了哲学思想。这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看作和理解为一个生动整体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一个生动整体理解和实践的理论。在这个阶段,根本不存在把这个整体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因素划分成单独的认识部门的问题,尽管每一种单独因素的每一个具体特点都受到忠实于历史的理解、分析和批判。当然,构成“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生动统一体的,不仅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这种最初的青年期的表现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是《共产党宣言》。[34]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最初表现形式不能经历19世纪下半叶的漫长岁月(实际上完全是不革命的)而不发生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整个人类说的话,也必然适用于当时正在缓慢地获得自我解放意识的工人阶级:“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句话并不因为一个超越现时关系的任务可能在以前时代已在理论上被提出而有所影响。赋予理论一种在现实运动以外的独立存在,显然既不会是唯物主义观点,也不会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观点;它只会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辩证观点毫无例外地从这一运动之流中去理解每一种形式,从辩证观点出发必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在它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受了相当大的变化。当马克思在1864年起草《成立宣言》和《第一国际章程》时,他完全意识到,“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35]当然不仅讲话是如此,关于这一运动的理论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也都一样。所以,1867—1894年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晚期著作的科学社会主义,与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或者《哲学的贫困》、《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直接革命共产主义比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的一种在许多方面不同的和更加发展了的表现形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特征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本质上也没有变。因为在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较发展的表现形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一种社会革命理论的包罗一切的整体。变化只是在于,在后一阶段,这个整体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它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相互分离了。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它的天然接合的脐带已被切断了。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决没有因此产生出独立因素的多样化来取代整体,而只是产生出这种体系的各种组成部分的另一种结合,它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上层建筑上,带有更大的科学精确性。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身在其创始者的著作中从未分解为一堆单独的认识部门,尽管对它的成果的实际的和外部的应用给人们暗示这样一种结论。例如,许多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者和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为,他们能够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区分历史材料和理论经济材料;但是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了,他们对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法一窍不通。因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根本没有这种区分;它的确在本质上就是对历史的东西的理论理解。此外,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第一种共产主义表现形式的最重要特征,在这个体系的后来的形式中也决没有被取消。只有肤浅的考察,才以为纯粹的思想理论似乎已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句话中都是潜伏的,然而又的确存在着,而且在每一个关键地方(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都一再迸发出来。我们只要想一想第24章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著名的第7节就够了。[36]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马克思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们不管如何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承认唯物史观,事实上却将社会革命的统一理论分解成为一些片断。在理论上以辩证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方式被理解的正确唯物史观,是与孤立和自立的单独学科、与脱离革命实践的在科学上客观的纯粹理论研究不相容的。可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系列与阶级斗争的政治实践或其他实践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纯科学认识。作为这点的证明,只要举出一个著作家、而且是在最好意义上富有代表性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阐述就够了。在1909年圣诞节,鲁·希法亭发表了企图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方面“进行科学理解,即把这些现象放到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去”的《金融资本》一书。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这里只需要说,对马克思主义说来,研究政治本身的目的只是为了发现因果联系。认识商品生产社会的规律,会立刻揭示出决定这个社会各阶级意志的因素。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科学的政治即描述因果联系的政治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决定各阶级意志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所以,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是错误,虽然这种做法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都极为普通。从逻辑上说,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因此与它的历史效果分开来考察的时候,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般提出的一种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则已把它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在一个生产商品的社会中发展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对实际行为的暗示。承认一种必然性是一回事,使自己为这种必然性服务是另一回事。一个人可能确信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又下决心去反对它,这是完全可能的。对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会给任何掌握这些规律的人保证优势。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那些从对它的认识中得益最多的人。”[37]按照希法亭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逻辑上说是“科学的、客观的、没有价值判断的科学”的理论。至于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他很容易地用“统治阶级极其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因此不愿“费力”去研究这种“复杂体系”来说明。“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敌人,因为它坚定不移地坚持每一种科学对其结论的客观和普遍有效性的要求。”[38]这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在他们的模仿者那里最终变成了非辩证的东西。对一种倾向说来,它变成了一种进行专门理论研究的启发原则。对另一种倾向说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灵活的方法论原则凝固成为一些关于社会不同领域的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理论原理——换句话说,变成了一种完全可以描述为一般系统社会学的东西。前一种倾向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只是看作康德意义上的“反思性判断力的主观原理”,[39]而后一种倾向则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教导主要看作是一种经济学体系,或者甚至是地理学和生物学体系。[40]这一切歪曲和一系列其他较次要的歪曲,是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二阶段上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它们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关于社会革命的统一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对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对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各种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不再必然发展成为革命实践;[41]它们同样能很好地发展成为各种基本上不越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之外的改良的努力,而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就是这种情况。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本身的这种歪曲(使它成为一种或者根本不再导致或者只是偶而导致实际革命行动的纯粹理论批判),如果我们将《共产党宣言》或者甚至由马克思起草的1864年《第一国际共同章程》同19世纪下半叶中欧和西欧各社会党的纲领、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达纲领(1875)和爱尔福特纲领(1891)中在政治领域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提出几乎完全改良主义的要求,是如何严厉批评的。这两个文件没有包含丝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革命原则。[42]的确,到上世纪末,这种情况使得正统马克思主义由于修正主义的进攻而发生了动摇。最后,在本世纪初,当暴风雨的最初征兆预告了更大的冲突和革命斗争的新时代即将来临时,这种情况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我们至今仍然处在这种危机中。
两个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总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发展的必然阶段——既然不言而喻,对辩证唯物主义说来,原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退为对社会的无任何革命后果的理论批判,是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平行发生的变化的必然表现。修正主义看来是企图以连贯理论的形式表达工联的经济斗争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下所获得的改良主义性质。这个时期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现在只是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看来大部分是一些背着传统包袱的理论家企图以纯粹理论的形式维持那种构成马克思主义第一种表现形式的社会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没有任何实践的意义——它只是力图拒绝各种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正性质被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在新的革命时期中,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最不能处理像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这种问题。修正主义者们至少拥有一种关于“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关系的理论,虽然这种理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长时期以来都用在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良来代替夺取、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并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它的社会革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把这种对过渡时期问题的解决办法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亵渎而加以拒绝。然而,不管他们如何正统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字面含义,他们不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革命性质。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不可避免地不再成为社会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缓慢地向全欧洲传播开来的漫长时期里,它实际上没有任何需要完成的实际革命任务。所以,对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正统派还是修正主义者说来,革命问题甚至在理论中也不再作为现实世界的问题存在。对改良主义者说来,这些问题已完全消失了。但是甚至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它们已完全失去了《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在谈论它们时的那种迫切性,而被推到遥远的、最后完全是虚无飘渺的未来中去了。[43]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实际上执行一种其理论表现可以被视为修正主义的政策。这种修正主义受到党的代表大会正式的谴责,最后受到工联同样正式的采用。在本世纪初,新的发展时期把社会革命问题作为一个现实的和尘世的问题全面地重新提上了日程。这样一来,纯粹理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直到世界大战爆发时在第二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式确立的形式)就完全崩溃瓦解了。这当然是它长期内部衰退的必然结果。[44]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在许多国家看到第三个发展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首先是由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常常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恢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变化和发展是在回到本来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学说的特殊意识形态伪装下实现的。然而,采用这种伪装的原因以及被它掩盖的过程的真实性质,都很容易理解。像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的列宁这样的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域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就是把它从第二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禁锢传统中解放出来。他们这样来回答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革命时期的实际需要,因为这些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劳动群众的头脑,他们的客观革命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再符合这些渐进的学说。[45]在第三国际中表面上恢复本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由于在新的革命时期中,不仅工人运动本身,而且作为这一运动的表现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都必须采取明确的革命形式。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看来实际上已被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很大部分今天又恢复了活力。也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领袖能够在十月革命之前几个月写出一本书,在其中说他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事态本身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为实践问题提上了日程。当列宁在决定性的时刻在理论上把这同一个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这已经是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在革命马克思主义内部有意识地重建起来的第一个证明。[46]
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问题的重新考察,看来也是这种恢复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否定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第二国际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轻视哲学问题,只是丧失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际革命性质的部分表现,它的一般表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原则同时在模仿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中消失了。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总是否认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哲学。但是很容易引用第一手资料来无可辩驳地证明,对革命辩证法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来,哲学的对立面的意思是与后来庸俗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意思很不相同的。没有什么比希法亭和第二国际大多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要求超乎阶级差别之上的、不偏不倚的纯粹理论研究更远离马克思和恩格斯了。[47]被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些不偏不倚的纯粹科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之间的对立,甚至比它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曾一度在其中找到自己最高理论表现的哲学之间的对立还要更尖锐得多。[48]因此,我们只能对最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缺乏洞察力感到吃惊,他们竟被马克思的一些人所共知的说法和恩格斯晚期的一些说法引入歧途,把马克思主义的废除哲学解释成这种哲学被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体系所取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所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真正对立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种革命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的完全废除,同时也将随着以它们为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结束。[49]
所以,即使纯粹在理论上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问题,以恢复被模仿者们歪曲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学说的正确和完整的含义,也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正像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问题上一样,这个理论任务实际上是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和压力下产生出来的。在革命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除了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必须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这一切任务常常是相互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又必须成为当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所认为的那种样子(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样子,而是通过辩证的发展):把社会一切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在内的社会革命理论。所以,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不仅解决“国家对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而且解决“意识形态对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时期中回避这些问题必定要导致机会主义,造成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危机,正像在第二国际中回避国家和革命的问题导致了机会主义,并且的确引起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危机一样。回避对这些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问题采取具体立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时期中能够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因为理论上的模糊和混乱能够严重妨碍及时而有力地处理那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政治问题一样受到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忽视。因此,在这个新的革命斗争时期中,必须把它重新提出来,必须恢复对它的本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即辩证的和革命的理解。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首先研究那个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意识形态问题的问题:哲学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关系是什么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对哲学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指出了,可以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推断出来。它将把我们引向一个更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对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什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哲学的关系是什么?庸俗马克思主义回答说:“没有任何关系。”按照这种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立场拒绝和克服了旧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一切哲学的思想和思辨因此被证明是仍然作为一种迷信纠缠着一些人的头脑的不现实的、空洞无物的幻想,统治阶级对保持它们有很现实的物质利益。一旦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被推翻,这些幻想的残余将立即消失。
人们只要像我们在上面试图做的那样,好好考虑一下这种对哲学的看法是何等肤浅,立刻就会认识到,这种对哲学问题的解决办法与马克思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它是属于“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杰里米·边沁在他的百科辞典中用“参看迷信观念”来注解“宗教”的那种时代的东西。[50]它是在17和18世纪所创造的那种气氛的一部分,这种气氛曾促使欧根·杜林在他的哲学中写道:在按他的方案建立的未来社会中,将不会有任何宗教膜拜;因为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会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会除去这种膜拜的一切组成部分。[51]现代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和这种对像宗教和哲学这类意识形态现象的浅薄的、唯理论的和纯粹消极的看法完全对立的。为了把这种对立充分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说: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说来,最重要的是把哲学及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在理论中作为现实理解,在实践中作为现实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就是以反对哲学现实的斗争开始了他们的整个革命活动的,我们在下面将表明,虽然他们后来彻底改变了他们对哲学意识形态在整个意识形态内部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的看法,他们一向是把各种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在内——作为具体的现实,而不是作为空洞的幻想对待的。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在理论和哲学方面开始了革命斗争,为争取解放这样一个阶级,它“不是同”整个现存社会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52]。他们确信,他们这样做是攻击了现存社会制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1842年《科伦日报》的社论中,马克思就已说过,“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53]。他后来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重复了这层意思:“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54]正是关于这部著作,马克思在15年以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他在那里最终实现了向他后来的唯物主义立场的过渡。正当辩证法家马克思实现这种从唯心主义观点向唯物主义观点的过渡时,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德国的实践派当时拒绝一切哲学,是和理论派未能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犯了同样的错误。后者相信,它能够从纯粹哲学的立场,即用以某种方式从哲学中得出的要求同德国这个世界的现实进行斗争(就像拉萨尔后来引用费希特的观点所做的那样)。它忘记了,哲学立场本身就属于德国这个世界。但是实践派基本上具有同样的局限性,因为它相信,“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它也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理论派错误地认为,“不(在理论上)消灭哲学,就能够(在实践上)使哲学成为现实”。实践派不(在理论上)使哲学变成现实(即不把它作为现实理解),就企图(在实践上)消灭哲学,是同样错误的。[55]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还有恩格斯,正如他和马克思后来常常解释的那样,他在这同一时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56])在何种意义上现已真正克服了他在大学生时代的仅仅哲学的立场;但是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克服本身在何种意义上仍然具有哲学的性质。我们有三个理由可以谈到对哲学立场的克服。第一,马克思现在的理论立场不是仅仅同德国一切现存哲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来,无论现在还是后来,这一哲学都是完全由黑格尔代表的)。第二,马克思不仅仅同只是现存世界的头脑或观念补充的哲学矛盾,而且同这个世界的整体矛盾。第三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矛盾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还是实践和行动上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然而,这种对纯粹哲学立场的一般克服仍然带有哲学性质。只要我们认识到,这种新的无产阶级科学尽管被马克思作为一种在倾向和目的上迥然不同的体系用来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然而在理论性质上与后者的差别何等之少,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德国唯心主义甚至在理论上始终有一种不只是理论、不只是哲学的倾向。根据上面讨论过的它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以后还要写一本著作来予以更详细的研究。这种倾向对黑格尔的前辈——康德、谢林、特别是费希特说来是很典型的。虽然黑格尔本人在表面上与此相反,然而他在实际上也给哲学指派了一个超出理论范围、在一定意义上是实际的任务。这个任务当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而是借助概念和理解把作为自我意识着的精神的理性同作为现存的现实世界的理性调和起来。[57]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并不因为承担这样一个世界观的任务(它无论如何通常被看作任何哲学的本质)而不再是哲学。同样,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仅仅因为有一个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标而不再是哲学,也是不对的。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中和那个时期其他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著作中所表述的那样,[58]按其本性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这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领域即哲学领域的斗争来参加在社会一切领域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制度的斗争。最后,它的目的是在废除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同时,具体废除作为这种社会现实的观念组成部分的哲学。用马克思的话说:“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因此,很清楚,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前进时,废除哲学对他们说来决不意味着简单地拒绝哲学。甚至当我们考虑他们后来的立场时,也必须时刻把下述这一情况作为出发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辩证法家,然后才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辩证的,那就会使他们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受到致命的和无法补救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及其他一切抽象的、不管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反,始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在理论上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并在实践上进行变革的唯物主义。因此,哲学就有可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变得不像它在开始时那样重要的社会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且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原则的过程中的确发生了。但是没有任何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然也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能够不再把哲学意识形态或一般意识形态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一种物质的组成部分,即一种必须用唯物主义理论理解并用唯物主义实践变革的现实成分。
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他的新唯物主义不仅同哲学唯心主义,而且同样尖锐地同一切现存的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同样,在他们后来的一切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在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通常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他们特别清楚,这种对立对于在理论上理解和在实践中处理所谓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现实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讨论一般精神表象和特别是具体和批判的宗教史所必需的方法时说道:“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59]按费尔巴哈的方式满足于把一切意识形态表象归结为它们的物质的世俗核心的理论方法,将是抽象的和非辩证的。仅限于反对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不关心改造和克服这些意识形态本身的革命实践,将同样是如此。当庸俗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现实采取这种抽象和消极的态度时,它同那些在过去和现在利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法律关系、国家形式和政治行动的论点来论证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该只限于直接经济行动的无产阶级理论家恰好犯了同样的错误。[60]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他与蒲鲁东等人的论战中尖锐地攻击了这类倾向。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中,只要他遇到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工团主义中仍然保留着),他总是强调指出,这样“先验地低估”国家和政治行动完全是非唯物主义的,因此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61]
这种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辩证看法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如此牢固的组成部分,甚至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实践中忽视革命过渡的问题,也不能否认这个问题至少在理论上的存在。不曾有过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在原则上声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关心政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是不必要的。这样做的只有工团主义者,他们中有些人援引马克思的话作根据,但是谁也没有声称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的确有许多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现实釆取了与工团主义者一样的理论和实践立场。这些唯物主义者与马克思站在一起谴责工团主义者拒绝政治行动,并且宣布社会运动必须包括政治运动。他们常常驳斥无政府主义者说,甚至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尽管资产阶级国家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政治还将在长时期内继续是一种现实。然而就是这些人,当他们听说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运动既不能被无产阶级单独的社会运动、也不能被它的联合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所取代或消灭时,立刻就会发作无政府工团主义对意识形态“先验地低估”的毛病。甚至在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从纯粹消极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意义上去理解所谓精神现象的现实性,而不是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教导的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的这一领域。精神生活应该与社会和政治生活连在一起去理解,最广泛意义的社会存在和生成(如经济、政治、法律等)应该与作为一般历史过程的真实的然而也是观念的(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社会意识连在一起去研究。然而他们不是这样,而是用完全抽象的和基本上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去看待一切意识,宣布一切意识是唯一真正现实的物质发展过程的反映,完全是不独立的,即使相对独立,归根结蒂也是不独立的。[62]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理论上恢复马克思所认为的理解和处理意识形态现实的唯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必然会遇到甚至比想要恢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要更大的理论障碍。模仿者在国家和政治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只是在于,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从未足够具体地论述革命过渡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然而,他们至少抽象地同意,而且在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漫长斗争中还特别强调指出,按照唯物史观,不仅构成其他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法律和国家、司法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现实。因此,它们不能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方式被忽视或弃之不顾:它们必须在现实中通过政治革命被推翻。相反,许多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至今还从来没有甚至在理论上承认精神生活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现实性。他们援引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某些说法,把社会的精神(意识形态)结构解释成只是一种虚假的现实,它只是作为错误、想象和幻想存在于意识形态家的头脑中,在现实中没有任何真正的对象。[63]无论如何,这应该适用于一切所谓“高级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观点说来,政治的和法的表象可能有意识形态的和不现实的性质,但是它们至少同某种现实的东西——构成该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法和国家制度——有关系。另一方面,“高级的”意识形态表象(人们的宗教、美学和哲学观念)不再和任何现实的对象相符。为了把这种想法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可以稍微夸大地说,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说来,有三个层次的现实:(1)经济,归根到底是唯一客观的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现实;(2)法律和国家,由于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已经不那么现实;(3)纯粹的意识形态,是无对象的和完全不现实的(“纯粹的胡说八道”)。
为了恢复对精神现实的真正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首先必须确定几个主要的术语。这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一般如何看待意识与其对象的关系。从术语上看,必须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想到把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只是描述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虚假意识,特别是那种赋予社会生活的局部现象以独立性质的意识。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表象就把法和国家看作是超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64]在马克思最确切地说明他的术语的那段话中,[65]他明确地说,在黑格尔称作市民社会的复杂的物质关系内部,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特别是,这些与法和国家同样现实的社会意识形式,包括商品拜物教、价值概念以及从它们当中产生的其他经济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分析了它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处理中特别有意义的是,他们从未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基本经济意识形态描述为意识形态。在他们的术语中,只有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学的或哲学的意识形式才是意识形态的。甚至这些意识形式也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而只是在上面已说过的一定前提下才是如此。在赋予经济意识形式的这种特殊地位中,清楚地表现出了把晚期完全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其早期的未发展形式区别开来的新的哲学观。从此以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哲学的批判,在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中退到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甚至可说是倒数第二位。《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曾认为是自己的基本任务的“批判的哲学”[66],变成了一种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抓住事物的根本[67]的更彻底的社会批判。马克思先前曾说过:“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68]但是他后来认识到了,任何法的关系、国家形式或者社会意识形式都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甚至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即从黑格尔和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来理解。因为它们根源于构成整个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物质生活条件。[69]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彻底批判,再也不能像马克思在1843年所说的那样把“任何”一种理论意识或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了。[70]它必须从那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科学表现的一定意识形式出发。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居于首位。然而,甚至马克思的革命社会批判的这种更深刻和更彻底的表现形式,也决没有停止为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从而对它的一切意识形式的批判。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似乎只是偶尔和顺便地批判哲学。实际上,他们决没有忽视这个问题,而是往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发展了他们对哲学的批判。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要针对今天关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广泛流行的某些错误概念,恢复它的全部革命意义就够了。这样做,同时也能澄清这种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这种批判与他对像哲学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关系。
一般都承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而且包括对它的一定社会意识形式的批判。甚至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纯粹而公正的“科学的科学”也承认这一事实。希法亭承认,对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表明“决定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的意志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意义上同时是一种“科学的政治”。尽管经济学和政治是这种关系,然而按照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概念,“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科学”具有纯粹理论的作用。它的职能是批判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把这种批判和科学研究的成果用于实际目的,即最终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经济结构及其生产关系。(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有时也能被西姆霍维奇或保尔·连施在实际上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本身。)
这种庸俗社会主义的主要弱点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它完全“非科学地”坚持一种素朴实在论,在这种素朴实在论中,所谓常识这种“最坏的形而上学者”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通常的实证科学都在意识和其对象之间画一条分明的分界线。它们都不知道,这种对立甚至对批判哲学的先验观点说来就已不再完全成立,[71]在辩证哲学中已被完全克服了。[72]它们至多以为,这种东西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可能出现。马克思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它们认为这就是这种神秘化,不言而喻,这种神秘化必须从辩证法的合理形式中,即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被彻底清除掉。我们将要表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他们的第一个(哲学)时期,而且在他们的第二个(实证科学)时期,都决没有任何这种对意识和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概念。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话可能遇到这种危险的误解。正因为如此,他们有时在自己的某些提法中的确为这种误解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借口(尽管这些提法可以很容易地被多一百倍的其他提法所纠正!)。因为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是包括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内的一切辩证法的特征。结果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是和它们反映在这个时期的科学以前的和资产阶级科学的意识之中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若没有这种意识形式,它们就不能在现实中存在。因此,把一切哲学考虑撇在一边,事情很清楚,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革命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反过来的情况就是:那些基本上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不到这种意识和现实一致的辩证概念有什么必要,因而最终把这种概念看成是在理论上错误的和非科学的概念。[7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革命活动的不同时期,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更高的政治和法律领域,进而在还要更高的艺术、宗教和哲学领域,都说到过意识和现实的关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注意这些话是针对什么说的(它们通常,尤其是在晚期,总只不过是些偶尔说的话!)。因为,根据它们所针对的对象是黑格尔和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和思辨的方法,还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夫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它们的意义是很不相同的。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后一种方法又在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中重新出现了,而且“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釆用的方法”。[74]从一开始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需要弄清的只是他们对第一种方法,即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立场。他们从未怀疑过他们是从它出发的。他们的唯一问题是必须对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进行什么样的改变,使之不再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是一种表面上唯心主义、然而暗地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方法,而变成为一种明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的指导原则。[75]黑格尔就已教导过,哲学和科学的方法不是一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于任何内容的单纯形式,而只不过是“全体的结构之展示在它自己的纯粹本质性里”[76]。马克思在一部早期著作中也说过意思相同的话:“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77]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它于是就变成一个“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78]的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碰到的,是黑格尔用以把辩证方法遗留给后代,而各种不同的黑格尔学派又以更加抽象更加形式的方式发展了的那种抽象思辨形式。因此他们说出像下面这样极其尖锐的话:一切思维只不过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思维的甚至最一般的范畴只不过是“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思维作为实在的东西所理解的对象“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79]然而,他们终生都拒绝那种把对直接现实的思维、观察、知觉和理解与这种现实对立起来、仿佛它们本身也是既与的独立本质的非辩证思想方法。这一点用恩格斯与杜林论战中的一段话可以最好地说明,由于按照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晚年的恩格斯与他的哲学伙伴马克思相反,退化到一种彻底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去了,这一段话就具有加倍的说服力,正是在这位晚年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描写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反对那种把意识和思维“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的完全“自然主义的”世界观。[8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不是抽象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所以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科学以前的、科学以外的和科学的意识[81]不再与自然的和尤其是社会历史的世界相对立地独立存在着。它们作为这个世界的现实的、客观的、“也是观念的”组成部分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独特差别。黑格尔曾说,个人的理论意识不能“跳过”他自己的时代,他当时的世界。然而他把世界置于哲学中,远远超过把哲学置于世界中。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间的这第一个差别,与第二个差别有密切的联系。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工人……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82]这段话以全部唯物主义的明确性说明了,由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现实现象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它的意识形式不能够单单通过思想来废除。只有同时实际而客观的推翻那些至今为止通过这些形式来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本身,才能够使这些意识形式在思想和意识中被废除。对于像宗教这样的最高的社会意识形式以及像家庭这样的中级的社会存在和意识说来,也是一样。[83]新唯物主义的这种结论包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马克思于1845年为了弄清自己的思想而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明确而全面的阐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如果以为这意味着实践的批判简单地取代理论的批判,那将是危险的误解。这种想法只是把对纯粹的理论的哲学抽象换成对同样纯粹的实践的对立的、反哲学的抽象。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说来,一切“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不是单单在“人的实践”中,而只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把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的辩证法翻译成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形式”,本质上意味着它已成为一种统一的既是理论和实践的又是批判和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即一种“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84]甚至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人一方面是思维,另一方面是意志,他一个口袋装着思维,另一个口袋装着意志,因为这是一种不实在的想法。”在黑格尔看来,“思维活动”中的概念(换句话说,哲学)的实际任务,不在于通常的“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语),而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85]与此相反,马克思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来结束对他自己的辩证方法的自我澄清:“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并不是像模仿者们所想象的那样把一切哲学都宣布为只是幻想。它并不是要绝对拒绝那基本上只是理解自身的哲学观念的思辨活动,而只是表示要绝对拒绝所有那些不同时是实践、即现实的、尘世的、此岸的、人的和感性的实践的理论,不管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理论批判和实际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割的活动,但不是在任何抽象意义上,而是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而现实的世界的具体而现实的变革。这句话以最确切的形式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
我们现在已经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则对理解意识和现实的关系的真正结论。我们同时也已经表明了在形形色色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流行的在对所谓精神现实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态度方面一切抽象的和非辩证的观点的错误。马克思的话不仅适用于狭义的经济意识形式,而且适用于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它们完全不是什么幻想,而是“高度客观高度实际的”社会现实,因此,“必须以实际和客观的方式来废除”。资产阶级健全理智的幼稚形而上学立场认为思维独立于存在,把真理确定为思维对外在于它并被它所“反映”的客体的符合。只有从这种世界观出发才能够坚持这样一种看法:一切经济意识形式(科学以前的和科学以外的意识以及科学经济学本身的经济概念)因为符合现实(它们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而具有客观意义,然而一切更高的表象形式只是无对象的幻想,在社会的经济结构被推翻、它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被废除以后,它们将自行化为它们现在本质上就是的那种乌有。经济观念本身只是看起来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之间具有映像与被它反映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在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一个整体的特定部分与这个整体的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连同物质生产关系属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整体也包含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及其外表的对象,这些东西被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法律家即“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语)以颠倒的意识形态方式看成是独立的本质。最后,这个整体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还要更高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到这些表象能够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地反映的对象,那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并没有独立存在的、与资产阶级社会其他现象分离开的特殊对象。把这种对象与这些表象对立起来,是一种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做法。这些表象只是以特殊的方式表达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艺术、宗教和哲学也是这样做的。它们在一起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精神结构与它的经济结构相符,就像它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这同一个基础相符一样。这一切形式都必须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社会批判,这种批判把整个社会现实都包括在内。这一切形式都必须与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结构一样并且与它们一起同时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上被推翻。[86]正像政治行动不会由于革命阶级的经济行动而变得不必要一样,精神行动也不会由于经济和政治行动而变得不必要。相反,它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被进行到底,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作为革命的科学批判和鼓动工作,在夺取政权之后则作为科学的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的专政。如果说这一般适用于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各种意识形式的精神行动,那么它也特别适用于哲学行动。正像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法律看起来凌驾于社会之上一样,资产阶级意识必然以为自己独立于世界之外,是纯粹的批判哲学和不偏不倚的科学。必须用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工人阶级的哲学同这种意识进行哲学的斗争。只有当整个现存社会及其经济基础已在实践中被完全推翻,这种意识已在理论上被完全克服和扬弃,这一斗争才会终止。“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注释:
[1]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9页。《全集》中的译文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录入者注
[2] 例如库·费舍在他的九卷本《近代哲学史》中用两卷论述黑格尔哲学,而在这两卷中只有一页篇幅(第1170页)是谈(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他把它们的创始人分别叫作斐·拉萨尔和卡·马克思:后者被他用两行文字打发掉。弗·恩格斯只是被他引证了,他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引证间接地中伤一下他的哲学同行。在宇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论:从19世纪至今》(1916年奥地利第11版)中,有两页(第208—209页)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教导;也有一处提到唯物史观,有几行文字说明它对哲学史有重要意义,并说它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的正好翻转过来的版本”。弗·阿·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只在一些说明历史情况的脚注中提到马克思,说他是“在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最大的行家”;他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理论家。这种态度对一些写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方面的专著的作者都是很典型的。参看本诺·厄德曼:《唯物史观的哲学前提》,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第31卷(1916年)第919页以后,特别是970—972页。下面还要提供更多的例子。
[3] 这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著名的最后一句话所明确指出的。类似的提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各个时期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可找到,例如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句话。
[4] 特别参看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恩格斯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发表的一篇论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的开头部分(指《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288页)。恩格斯显然完全同意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把“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的1848年前的德国社会主义描写为“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他把这一派的追随者称作“过去的哲学家”,并且直截了当地把他们同他认为构成在1848年融合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两派中另一派的“工人”相对比。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29页。
[6] 《新时代》第1卷,第28期,第686页。在梅林的《马克思传》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那一章第116—117页有类似的说法。若把这些说法与古斯塔夫·迈尔的《恩格斯传》(1920年)的相应章节(第234—261页)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梅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著作的意义是多么不理解(可惜这些著作至今还没有全文发表)。
[7] 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例子是一场小冲突,在《新时代》第1卷第26期,第695和898页上可以找到它的痕迹。编辑部(卡尔·考茨基)在发表波格丹诺夫论述《恩斯特·马赫与革命》的文章时,在它前面刊载了译者加的一段按语。那个未具名的译者感到必须责备俄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极其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是与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一致还是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一致这种在我们看来同它完全无关的问题的争论”而“加剧”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即列宁)被迫对此作出答复,并且声明:“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照编辑部的意见,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405页)。然而,大家都很清楚,写了这篇正式辟谣声明的人,即伟大的策略家列宁,在这同一年稍后的时候却发表了他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8] 他们把这点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弱点,而不是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看作由哲学向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长处;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力图拯救社会主义理论其余内容的全部或部分。他们在资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之间的战斗中,从一开始就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对手的一边。他们只是尽可能避免作出必然的结论。但是1914年以后危机和战争的事实使人们不可能继续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于是一切种类的哲学社会主义的真正性质就变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仅像伯恩施坦和克尼希这样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哲理社会主义者,而且大多数哲理马克思主义者(康德派、狄慈根派和马赫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那以后都用言论和行动表明了,他们没有真的脱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这不仅适用于他们的哲学,而且必然也适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必为康德派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提供例子,因为对它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怀疑。至于马赫派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将它的追随者引上(而且已经把他们的大部分人引上了)的道路,列宁在他1908年与经验批判主义的争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狄慈根派马克思主义已经沿着这同一条道路走了一段,这是狄慈根的儿子所写的一本小册子(1923年)表明了的。这个颇为幼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仅仅祝贺他的“保证人”考茨基放弃了大部分“旧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还对考茨基在重新学了那么多以后,仍然要保留这些立场的某些痕迹表示惋惜(第2页)。但是大卫·克尼希的例子最好地说明了,当梅林面对着像这样的哲学幻想完全拒绝了一切哲学时,他的政治本能是多么健全。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读一读梅林对克尼希的完全不成熟的早期哲学著作所作的极其审慎的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第1卷,第20期,第385页以后,和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第2卷,第348页),并且了解到这个哲学家是如何迅速地在伯恩施坦的庇护下(1903年)发展成了最肤浅的“文化社会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变成了最糊涂和反动的浪漫派之一。(关于这最后的阶段,可参看克尼希发表在《政治杂志》1922年,第304页以后的文章。)
[9] 恩格斯:《反杜林论》1885年第2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马克思在《资本论》1873年第2版跋的末尾有类似论述。
[10] 这点的最好例子是埃·冯·西多夫在他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理想王国思想》(1914年)第2—3页上说的如下一段话:“只要理想的思想历史化了,它就失去了它的爆炸力,因为在德国唯心主义中,是理想使历史成为逻辑的,并且把它从‘一串事实’变为‘一系列概念’。如果理想是逻辑和历史的必然,那么为它奋斗就是过早的和没有意义的事情。对理想概念的这种说明是绝对唯心主义者的成就。如果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在可见的未来仍然占统治地位,我们必须感谢他们。当统治阶级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幻影,常常把他们的行动意志变为行动勇气的时候,无产阶级却依然相信从唯心主义体系中得出的唯物主义破烂。但愿这种可喜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正像在所有其他的原则问题上一样,对这一成就做出贡献最大的是费希特。”冯·西多夫在一个脚注中很明确地指出,这一事实“可以用来反对那些或多或少公开宣称哲学在政治上不重要的人们”。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59页。——录入者注
[12] 关于这一点,参看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2012),特别是第695—696、698页(关于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人物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60页(关于哲学)。这里还可以参看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那里一般地批评了这样一种做法,即用“哲学家个人的良心受到怀疑”来解释哲学家的错误,而不是客观地“找出他的本质的意识形式、将之提升为确定的形态和意义,并从而克服它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4—75页)。
[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9页脚注89。马克思在那里讨论宗教史时,把他提出的方法描述为“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下面还要更详细地谈到这点。
[1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0页。
[15] 康德也喜欢在纯思想领域使用“革命”这种说法,但是应该说,他的意思比今天资产阶级的康德学者说的要更具体得多。应该把它同康德在《学科之争》和在其他地方关于现实革命事件的许多说法联系起来理解,如:“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他宣称,“在所有旁观者(他们自己并没有卷入这场戏)的心灵中获得了一种同情,这种同情几乎接近于狂热。”“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种现象不再被遗忘。”“那个事件太重大了,与人类的兴趣交织得太紧密了,按照其影响它广泛地传播到世界上的所有地区,以至于它在有利情况的某种诱使下不会不被各国人民想起,并唤起他们去重复这一类的新尝试。”(以上引文分别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85页)康德的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收集在盖斯马尔编的《18世纪德国人的政治著作》(1847年!)第1卷,第121页以后。
[16] 黑格尔,前引著作第240页。大家都很了解,马克思完全采用了并且有意识地发挥了黑格尔这个关于德国人和法国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总过程中分担了不同角色的观点。参看他早期的全部著作(梅林编的《遗著》第1卷),那里例如可以看到下述这类说法:“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因此德国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命运就在于“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所有这些话都出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01、207、209页)。
[1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14页。
[18] 参看《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表述黑格尔关于哲学和现实的辩证关系的思想的有名的话;它是把黑格尔的仍然有点神秘化的表述方式(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自己的时代”)转译成了合理的形式:“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5页;第3版,第1卷,第413—414页)。
[19] “黑格尔哲学瓦解的产物”(流行的观点)。“德国唯心主义巨人的堕落”(普伦格)。“一种扎根于价值的否定之中的世界观”(舒尔采-格弗尼茨)。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从德国唯心主义的高峰跌落到它的唯物主义地狱的无底深渊中去的邪恶精灵。这种观点的荒唐由下述这一事实特别淸楚地表明了,即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可以看得出这种跌落的影响的方面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些体系中已经包含了的,马克思采用时并未作任何明显的改变,例如,关于恶对人类发展是必然的思想(康德、黑格尔);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财富不断增长和贫困不断增长之间有必然联系的思想(黑格尔,《法哲学》第243—245节)。资产阶级在它最发展的阶段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对它内部包含的阶级矛盾的一定意识。资产阶级意识把这些矛盾看成是绝对的,因此认为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先进的地方在于,他不再把这些矛盾看作自然的和绝对的,而是看作历史的和相对的,因此它们能够被较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消灭。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忽视这一点,仍然从狭隘的、否定的和颠倒的资产阶级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
[2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55、364页及以后几页(《反杜林论》)。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在理论上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来源,见恩格斯在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序言加的脚注中的说明;又见他对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54页以后)。
[21] 下面要讨论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自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见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通过对黑格尔以后的全部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形式放弃了他们“以前的”哲学观点,也是在这一年。从那时以后,他们在哲学问题上进行论战的目的就只是启发或消灭他们的敌人(如蒲鲁东、拉萨尔和杜林),而不再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
[22] 首先参看《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20—421页)。“‘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別,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哲学或宗教的关系基本上同它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经济意识形态、对商品拜物教或价值的关系是一样的。再参看《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92页以后各页,特别是注31和注33)和马克思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5页以后[价值],第27页以后[国家]和第31页以后[宗教])。
[23] 参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随处可见)。
[24] 例如,参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听起来有点意识形态味道的说法:“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26页)
[25] 的确有一些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真的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废除国家(不是反对国家的特定历史形式),只有名词术语上的意义!
[26] 特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394—400页(《反杜林论》)和第4卷,第264页(《费尔巴哈论》)。这两处的论述内容相同,下面的话引自《反杜林论》:“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对历史和自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毎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400页)
[27] 恩格斯的论述,从上面援引的形式看,显然只不过包含名称的改变,在恩格斯声称是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结果的东西同无论如何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应得出的和黑格尔已经说是他的辩证唯心主义立场的结果的东西之间,看来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差别。甚至黑格尔也要求每一门科学弄清自己在总联系中的地位,然后他按照下述思路继续论述:因此毎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从字面上看,这里发生的与恩格斯的哲学变为科学正好相反;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两人看来是说的同一回事。两个人都要清除在各个特殊科学和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通过把个别科学纳入哲学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而恩格斯则把哲学融解在个别科学之中。在两种情况下,结果看来完全一样:个别科学不再是特殊的科学,同时哲学也不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专门科学。然而我们以后就会看出,在黑格尔和恩格斯之间这个似乎纯粹字面的差别后面有更多的东西。这个差别在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尤其是在他后来的一些提法中,不像在早期马克思一人或和恩格斯合作写的著作中表达得那么清楚。这里重要的是,不管恩格斯如何承认“实证科学”,他仍然要在“哲学”内部保存一个一定的、有限的领域的独立性(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里的重要问题当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到底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28] 我们后面将看到,甚至一些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不幸地接近采取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的看法。而且上面援引的老年恩格斯的话(注26)可以被解释成这样的意思:在本质上,哲学已被黑格尔本人以精神方式无意识地克服和扬弃,后来又由于发现唯物主义原则而被有意识地克服和扬弃。然而,我们将看到,不管现象如何,恩格斯表达这点的方式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的真正含义表达出来。
[2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8页以后。
[30]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译者注
[31] 关于这三种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初如何相互冲突的情况,参看伦纳:《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考茨基驳伦纳的著作:《战争社会主义》,载《马克思研究》,维也纳版第4辑第1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反潮流》文集中对伦纳、考茨基等人的论战。
[32] 参看考茨基:《马克思主义中的三次危机》,载《新时代》,第1卷,第21期(1903)第723页以后。
[33] 对列宁著作的实践和理论背景没有比较深刻理解的人可能以为,列宁事实上采取了这样一种道德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立场。可能使他们产生误解的,是列宁(在这方面是马克思的忠实门徒)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的极端尖锐的和人身攻击的方式,以及列宁在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时所表现出的渊博和准确性。然后较仔细地阅读就会看得很清楚,列宁从未使用个人因素来说明这个几十年来在国际范围内展开的,并且在19世纪下半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贫乏和退化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他使用这个因素只限于说明在世界大战前政治和社会危机迫在眉睫的最后时期中的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如果声称列宁认为偶然性和个人特点对世界历史或者对说明特定历史现象毫不重要,那也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参看马克思1871年4月17日那封致库格曼的著名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3—354页;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格言式的结尾部分中关于“承认偶然”等的很一般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1页)。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说明的时期越长,个人因素的说明作用不言而喻必定越不重要。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列宁在其全部著作中一向是按这种真正“唯物主义”方式行事的。但是《国家与革命》的序言和第一页证明,他决不认为这部理论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重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34] 但是,像《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种较后期的著作,在历史上也属于这个阶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453页(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这段话对于正确理解《成立宣言》非常重要,然而考茨基在给他的1922年版《通信集》写的序言(第4—5页)中援引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时作了很大的刪节。他这样把1864年《成立宣言》的调子压低以后,就能够(第11页以后)用它来反对1847—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火热风格和“第三国际的非法代理人”。
[36] 在论工作日的第8章末尾有关于这点的其他好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5页):“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还可参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篇中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著名段落。在《资本论》中类似的论述如此之多,完全没有必要提到像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宣言(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类晚期的直接革命著作。
[37] 参见《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前言第3—4页。
[38] 直到1914或1918年,无产阶级读者都可能以为,希法亭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们的著作有客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即与任何阶级基础无关),是出于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实际的和策略的考虑。像保尔·连施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例子表明,这类“科学认识”可以“很好地”被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顺便还可以提一下,这里批评的希法亭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间作的区分,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西姆霍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一书中发展到最荒谬的结论。这本书于1913年在伦敦出版,单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是一本很独特而有趣的书。马·鲁宾诺夫在《根据现代统计学看马克思的预言》一文(载格律恩贝格:《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第6辑,第129—156页)中对该书作了详细的评论。
[39] 参看《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节,第250—251页。康德在同一段话里把这个准则描述为“研究自然的指导”;同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把他阐述他的唯物史观的那一段话,描述为是从他的哲学和科学研究中得出的对进一步研究的“指导”。那么人们可以说,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原则只是看作研究社会的一种指导,就像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一种指导一样。人们也可以援引马克思批驳那些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包含有先验因素或者抽象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批评者们的一切论述作为对此的进一步证明。(参看《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8—20页;和1877年11月一封关于米哈洛夫斯基的著名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126页以后)。然而,在我去年的著作《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1922年柏林版)中已说得很清楚,为什么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看作纯粹启发性的原则是不恰当的(特別参看第16页以后和头两个附录)。
[40] 特别参看我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的序言和第18页以后对路德维希·沃尔特曼的批判。有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实践中属于革命共产主义,但是非常接近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一般社会学”等同起来。参看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69年安·阿博尔平装本)第13—14页和卡·威特弗格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1922年版)第50页。
[41] 马克思说,对现代国家、对与之有关的现实以及对德国以往一切政治和法律意识的批判应该发展成一种“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发展成一种革命,而且不是“部分的、仅仅政治的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进行的,不仅解放政治的人,而且解放整个社会的人的革命(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06页以后的几页)。
[42] 参看我编辑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922年柏林版)中所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352页以后)以及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页以后)。
[43] 参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批评过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2页)考茨基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第172页上的一句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44] 参看考茨基在他最近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中提出的对马克思专政学说的“改变”:“马克思在他的名著《社会民主党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改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根据近年来有关政府问题的经验,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原理改成这样:‘在民主国家的纯粹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和纯粹无产阶级统治时代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政府通常将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1922年版第196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页以后。
[46] 列宁1917年11月30日在彼得格勒为《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写的跋中,用几句话最清楚地说明了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16页),“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47] 暂时只参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即各种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关系的论述,以及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与空论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相对立的评论:“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234—236页)。
[48] 参看我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第7页以后各页。
[49] 后面将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实证科学”的确只有这个意思。同时,那些持有上面讨论的那种看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一位资产阶级马克思研究者那里了解到自己所犯的可怕错误。瑞典人斯汶·赫兰德写的《马克思与黑格尔》(1922年耶拿版)是一本极其肤浅的著作,而且错误连篇,但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他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理解,比其他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批评家和通常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要深刻得多。这本书中有令人信服的证据(第25页以后),表明我们只有在黑格尔“批评社会批评家并劝他们研究科学和学会理解国家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防止吹毛求疵”的意义上,才能谈论“科学社会主义”。这段话很能说明赫兰德这本书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他没有提供黑格尔这些论述的出处;事实上,它们是出自《法哲学》的序言。但是黑格尔在那里说的不是科学,而是哲学。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意义不是像黑格尔眼中的哲学的意义那样与现实调和,而是彻底改变这一现实。(参看注47从《哲学的贫困》中援引的那段话。)
[5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03—705页关于边沁的评论。
[5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703—705页关于这个问题的尖刻讽刺。
[5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13页。
[53]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20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06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06页。
[5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3—414页。
[57]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14—15页)和上面注49中关于赫兰德的评论。
[58] 除了多次提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外,这里还包括1843—1844年对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的批判,1844年对神圣家族的批判,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两人合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他们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总清算。这部著作对当前讨论的重要性,从《神圣家族》序言中的一处说明已可看出,两位作者在那里说,他们以后的著作将叙述他们自己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肯定的见解,从而说明他们对这些学说的肯定关系。这部著作对于详细地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很遗憾,它还没有全文发表。但是,甚至那些已发表的部分(特别是《圣麦克斯》和《莱比锡宗教会议》)以及古斯塔夫·迈尔在他的《恩格斯传》中对这部手稿未发表部分的极其有趣的介绍(德文版第239—260页),已使我们能够看出,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全面阐述。对《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这样说,那里阐述的唯物主义原则基本上是片面的:不是突出它的实践和革命的一面,就是突出它的理论、经济和历史的一面。《〈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几句表达唯物史观的著名的话,只是为了把马克思用来分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社会的指导”提供给读者。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打算在这段话里充分表述他的整个新辩证唯物义原则。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虽然不论是从这些话的内容还是从它们的语气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马克思说,在社会革命时期人们将意识到已经开始的冲突并且参加进去;人类只在一定条件下提出一定的任务;而且革命时期本身有一定的意识。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用根本没有讨论历史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有历史主体或是在正确意识下或是在错误意识下实现社会的发展。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如果想要看到作为整体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就必须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特别是上面已提到过的头一个时期的著作(以及《资本论》和晚期一些篇幅较短的历史著作)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关于唯物史观的描述,来对这点加以补充。我在去年(1922)出版的一本小书《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就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初步的尝试。
[59]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9页注89),还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4条也说的是同一回事。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就是同有缺陷的抽象唯物主义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还可参看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41页以后),他在那里谈到梅林在《莱辛传奇》中运用难物主义方法时所忽略的、“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的地方。“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的著作所作的这种自我批评,实际上只在很小的程度上适用于他和马克思使用的方法。他所批评的片面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比在恩格斯自己的著作中少得无可比拟,就是在恩格斯那里也远远没有按照他的尖锐的自我批评可能料想的那样多。恩格斯害怕他对这个形式方面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这使得他在晚年犯了有时以不正确的、非辨证的方式对待这个形式方面的错误。我这里指的是在《反杜林论》和《路徳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特别是在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所有涉及“唯物史观的有效范围”的段落;这些书信由伯恩施坦收在《社会主义文献》第2卷中(第65页以后)。恩格斯在这些段落中倾向于犯那种被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第156节中描写为“完全没有概念的态度”的错误。用黑格尔的术语说,他从概念的高度后退到概念的门口,后退到交互关系和交互作用的范畴等等(参见《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60] 这种过时观点的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可以在蒲鲁东1846年5月那封著名的信中找到,他在那里向马克思解释他在当时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遗著》第2卷,第336页):“借助一个经济组合把被另一个经济组合从社会中取走的财富退还给社会;换句话说,把所有制理论转变成政治经济学,使之反对所有制,从而达到你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所谓的财产共有。”相反,马克思当时虽然肯定还没有达到他后来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然而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促使经济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按政治方式提出和解决的辩证关系。参看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他在那里谈到那些认为像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这类政治问题“不值得注意”的“极端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用辩证的考虑回答说,“这个问题只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表明人的统治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5—66页)。
[61] 特别参看《哲学的贫困》的最后几页。
[62] 关于恩格斯晚年对这种见解最后作了多大程度让步的问题,参看注59。
[63] 大家知道,恩格斯后来曾经谈到像宗教、哲学等这种“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说它们包含有“原始状态的愚昧”的史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11—612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也以类似的显然完全消极的口气专门谈到哲学。
[64] 特别参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国家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59—260页)。
[65]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12卷,第82页)。在资产阶级马克思研究者汉马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体系》(1909)一书第190—206页可以看到很仔细地汇集到一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语文学和方法论的资料。汉马赫与其他资产阶级马克思批评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在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时,至少引用了全部原始材料,而其他人,例如托尼斯和巴尔特,则把他们的解释建立在马克思的个别句子和段落的基础上。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7页。
[67]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是这样给“彻底”这个词下定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07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5页。
[6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413页;第30卷,第50—51页。
[70] 这不是对马克思的真正立场(甚至1843年的立场)的完全确切的说明。文中引用的话出自马克思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但是在几行之前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的代表人物所关心的问题涉及真正人类本质的实际存在。然而,他们也需要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另一方面,即人在宗教、科学等当中的理论存在。马克思的发展可以归纳如下。首先,他对宗教进行哲学的批判。然后,他对宗教和哲学进行政治的批判。最后,他对宗教、哲学、政治及其他一切意识形态进行经济的批判。这条道路上的里程碑是:(1)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序言中的评论(对宗教的哲学批判)。(2)他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关于费尔巴哈的评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还有在常常被引用的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的一句有名的话,即哲学已经“世俗化”了,从而“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看法:“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已经被“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所提出,但是它站在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甚至是它在黑格尔著作中的“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阐述”的现实水平之外(以上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0—12页;第47卷,第53、64页;第3卷,第204—206页)。
[71] 拉斯克在这方面的意见特别富有教益(他的《法哲学》的第2节,《献给库诺·费舍的纪念文集》第2卷,第28页以后)。
[72] 受过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和方法深刻影响的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将军著的《战争论》第2篇第3章,为这点提供了很出色的说明。克劳塞维茨就应该说军事艺术还是应该说军事科学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使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比使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更恰当些”。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继续说,严格考察起来,战争既不是真正的艺术,也不是真正的科学,按它现代的形式也不是一种“手艺”(在佣兵队长时期是如此)。事实上,战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类交往的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战争不属于艺术或科学的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战争与其说像某种艺术,还不如说像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治,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有些受僵硬的形而上学范畴影响的现代实证主义思想家,满可以这样指责这一理论:这位著名的作者把军事科学的对象与军事科学混为一谈了。其实,克劳塞维茨知道得非常清楚,科学在通常的和非辩证的意义上指的是什么。他很明确地说,不可能有把通常称作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的东西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真正的”科学。这是因为它既不像机械的艺术(和科学)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像观念的艺术(和科学)那样,处理的是“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像没有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任何对象一样,它是能“用研究精神阐明的,它的内在联系是或多或少可以弄清楚的”,而且“只要做一点,理论就是名副其实的理论了”(参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第176—180页)。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概念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理论概念是如此相似,没有必要再说什么。这丝毫不足为奇,因为它们两者出自同一个来源:黑格尔对哲学和科学的辩证概念。此外,克劳塞维茨的模仿者对他们大师的理论的这一方面的评论,在语调和内容上也与某些现代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理论的看法惊人地相似。这里是施里芬给克劳塞维茨著作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克劳塞维茨并不否认正确理论本身的价值,但是他的书《战争论》贯穿了使理论与现实世界协调一致的努力。部分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书中常常以哲学家的态度探讨问题,而这并不总是投合现代读者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下半叶不单是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了。
[73] 在不革命精神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方面的完全误解之间的这种联系,在爱德华·伯恩施坦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他关于价值理论不同方面的阐述末尾(《社会主义文献集》第5卷1905年版第559页)有一句与马克思的价值论真谛大相径庭的话:“今天我们(!)研究价格形成的规律,是采取更直接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那种称作‘价值’的形而上学对象的迷宫。”同样,回到康德去的以及其他倾向的社会主义唯心主义者把“是”和“应该”分隔开来。参看赫兰德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第26页上的幼稚批评:“大多数人自然(!)惯于按康德的方式思考,即承认‘是’和‘应该’之间的差别。”还可参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约翰·洛克的评论,他在那里说,这位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2页)。
[74] 在恩格斯于1859年8月6日和20日在伦敦一家德文周刊《人民报》上发表的两篇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的第二篇中,可以看到对这整个方法论情况的最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6页以后)。这里引用的话和其他许多类似的话可在第10页以后看到(“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这时,“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自然科学“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包括沃尔夫式的极端浅薄的陈词滥调,也就重新流行起来”;“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等等)。
[75] 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逻辑方法之间的关系,参看恩格斯的上面注中提到的那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13页)。
[76] 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页。
[77]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8页)。黑格尔那句话(出自《精神现象学》)在我的《唯物史观核心观点》第38页全文引出了。不能理解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这种同一关系,是先验观点不同于辩证观点(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之处。前者把内容看作是经验的和历史的,把形式看作是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后者使形式也从属于经验和历史的暂时性,从而从属于“斗争的漩涡”。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纯粹民主和纯粹先验哲学是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78] 上面提到的恩格斯的那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13页)。恩格斯接着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制定这个方法,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还可参看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1873年第五版跋中的人所共知的说法。
[79] 所有这几段话都出自马克思逝世后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供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方法论立场的最丰富资料。
[80]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38页)。更仔细地分析恩格斯的这些话和他的其他晚期著作,可以看出他只是强调马克思在世时就已存在的一种倾向。他在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包括意识的社会历史形成)“归根到底”由经济决定的“最后决定”之外,又加上一种“由自然界决定的”甚至“更加最后的决定(!)”。恩格斯这最后的一着发展和维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正如文中援引的那段话清楚地表明,它丝毫没有改变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概念。
[81] “科学以前的概念的形成”这个名词,大家知道是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提出的。实质上,在把先验立场或辩证立场用于社会科学而一切地方,很自然地必定要出现概念(例如在狄尔泰那里)。马克思把“思维着的头脑对世界的精神掌握”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严格而确切地区分开来(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3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83] 关于新唯物主义立场对宗教和家庭的结论的发展情况,首先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4条,然后参看《资本论》的不同地方。
[84] 参看《资本论》1873年第2版跋末尾那些常被引用的话。
[85]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节补充的一段和序言的最后几段。
[86] 特别参看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的论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附录:
部分译名对照表
B
巴尔特〔Barth〕《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C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理想王国思想》〔Der Gedanke des Ideal-Reichs in de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von Kant bis Hegel〕E
厄德曼,本诺〔Benno Erdmann,1851—1921〕《恩格斯传》〔Friedrich Engels, eine Biographie〕
《恩斯特·马赫与革命》〔Ernst Mach und die Revolution〕
F
《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费舍,库诺〔Kuno Fischer,1824—1907〕
G
盖斯马尔,马丁·冯(埃德加·鲍威尔的化名)〔Martin von Geismar,=Edgar Bauer,1820—1886〕格律恩贝格,卡尔〔Carl Grünberg,1861—1940〕
《根据现代统计学看马克思的预言》〔Marx' Prophezeiungen im Lichte der modernen Statistik〕
H
汉马赫,埃米尔〔Emil Hammacher,1885—1916〕赫兰德,斯汶〔Sven Heiander〕
J
《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phie〕K
克尼希,大卫〔David Koigen,1879—1933〕L
拉斯克,埃米尔〔Emil Lask,1875—1915〕《莱辛传奇》〔Die Lessing-Legende〕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
《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e〕
鲁宾诺夫,伊萨克·马克斯(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中,为J.M.Rubinow [New York],恐为误)〔Isaac Max Rubinow,1875—1936〕
M
《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马克思与黑格尔》〔Marx und Hegel〕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体系》〔Das Philosophisch-ökonomische System Des Marxismus〕
《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马克思传》〔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迈尔,古斯塔夫〔Gustav Mayer,1871—1948〕
P
普伦格,约翰·马克斯·伊曼努尔〔Johann Max Emanuel Plenge,1874—1963〕R
《人民报》〔Das Volk〕S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社会主义文献》〔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18世纪德国人的政治著作》〔Die Politische Literatur Der Deutschen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舒尔采-格弗尼茨,格哈特·冯〔Gerhart von Schulze-Gävernitz,1864—1943〕
T
托尼斯,费迪南德〔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W
威特弗格,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唯物史观的哲学前提》〔Die philosoph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原理》)〔Тео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Der Stand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沃尔特曼,路德维希〔Ludwig Woltmann,1871—1907〕
《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X
西多夫,埃卡特·冯〔Eckart von Sydow,1885—1942〕《献给库诺·费舍的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Kuno Fischer〕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us〕
《学科之争》〔Streit der Fakultäten〕
Y
《1892年工人党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 pour 1892〕《遗著》(即《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著作遗产》)〔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宇伯威格,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Ueberweg,1826—1871〕
Z
《战争论》〔Vom Kriege〕《战争社会主义》〔Kriegssozialismus〕
《哲学史概论:从19世纪初至今》〔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eil 4: Vom Beginn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auf die Gegenwart.〕
《政治杂志》〔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Die Wissenschaf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